電影是一個神奇的東西,一個好的電影導演就像一個琴手,一個畫師,只要輕輕撥一下,抹一筆,你的心弦就震顫了,你的視線就模糊了。於是,整個世界縮小在那塊幕布上,也放大在那塊幕布上。
關錦鵬就是這樣一位導演。他的風格婉約,手法細膩。十多年前看他的電影,就沉浸在那種唯美當中,後來隨著歲月的流逝,年紀的增長,這個世界在眼中反倒變得模糊不清起來,再看關錦鵬的電影,總覺得當中有一種特殊的信息要傳達給我們。這特殊的信息到底是甚麼呢?
從理到文,從台前到幕後
眼前的關錦鵬戴一副無框眼鏡,微胖,看著很斯文很學術,很像高中裡的班主任。
他1957年生於香港,祖籍廣東。
關錦鵬就讀的培正中學,以數理成績好而著稱。從初一到高二,他念的都是理科。高二結束的那個暑假特別長,他於是參加了一個話劇團,發現自己對文藝很感興趣,想要改變職業方向。母親很生氣,她希望長子將來做個醫生。
但是關錦鵬堅持自己的理想,他與幾個同學一起去考了無線的藝員訓練班,順利被錄取。同一年,也考入香港浸信會大學傳理系。
當時無線受訓只要1年時間,於是關錦鵬就讀了下去,入大學後兩邊兼修。
訓練中,關錦鵬發現自己並不上鏡,便申請調到幕後。 恰好躬逢「新浪潮」年代,無線很多導演如徐克、許鞍華等人從國外回流,香港電影開始從電視業醞釀她輝煌的80-90高峰。
恰好躬逢「新浪潮」年代,無線很多導演如徐克、許鞍華等人從國外回流,香港電影開始從電視業醞釀她輝煌的80-90高峰。
關錦鵬回憶,「那時我大多是當場記或者助理編導,但是這些經歷對我後來擔任電影的副導演都很有幫助。那時無線很多導演,如徐克、許鞍華、嚴浩、譚家明等人剛從國外回來,他們使用16釐米攝影機拍攝大量單元劇集,叫做film unite,我跟他們工作了很長時間,這些經驗和後來電影的工作環境非常接近。」
在無線工作的最後幾年,關錦鵬開始了他和許鞍華導演的長期合作。「其實許鞍華籌拍《瘋劫》時,已經找我去做副導,但是當時我剛好在幫另一個導演,於是錯過。後來她又籌備《小姐撞到鬼》(又名《撞到正》),仍然來找我,時間上我已經可以了。」
在正式合作之前,許鞍華邀請關錦鵬去看《瘋劫》首映,「我看了之後覺得,哎,這個導演我要跟她學學,應該可以學到很多東西。於是開始了我和許鞍華之間的多年合作。」
「如果許鞍華肯認我這個徒弟的話,她絕對是我的師傅。」80年代初,關錦鵬跟著許鞍華做了四年半的副導演,有過「副導演王」的美譽。新浪潮電影的代表人物,如今有的進了大學教書,有的改行經營起房地產,還在堅持拍片的人中,許鞍華就是一個,盡管她常常對關錦鵬一聲三嘆體力不濟(有大學邀請她去做教授)。「電影對於她而言,是條不歸路。」關錦鵬充滿敬意之餘,常常想起師傅的一句話:「每拍一部片,你要跟自己說,這也許就是最後一部。」
巧手編製,女性題材電影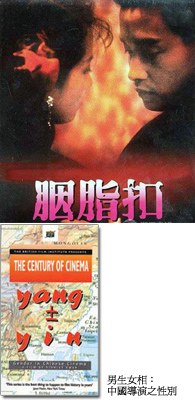 一九八五年,關錦鵬憑借一炮而紅的處女作《女人心》正式開始了自己的導演生涯。其後更以《胭脂扣》、《阮玲玉》、《紅玫瑰白玫瑰》等片晉升為國際級的大導演。其婉約、細膩而深刻的風格,被視為女性電影的代表。
一九八五年,關錦鵬憑借一炮而紅的處女作《女人心》正式開始了自己的導演生涯。其後更以《胭脂扣》、《阮玲玉》、《紅玫瑰白玫瑰》等片晉升為國際級的大導演。其婉約、細膩而深刻的風格,被視為女性電影的代表。
1996年,為紀念世界電影100年,英國電影協會在全世界範圍內邀請了12位導演各拍一部紀錄片。美國是馬丁·西科塞斯,日本是大島渚,所幸中國電影沒有缺席,百年電影史的建構工程,落到了香港導演關錦鵬身上。他當年完成了一部概觀兩岸三地電影的神采飛揚的紀錄片《男生女相:中國導演之性別》。作品一完成,便入選威尼斯影展「窗口」單元。
台灣著名影評人焦雄屏激情點評:「在關錦鵬所有作品中,這部紀錄片絕對是有代表性的。關錦鵬巧手編織,用性別的角度切入中國電影史,既個人又群體,既主觀又客觀,娓娓述來,有條不紊,讓人看到中國電影是那麼迷人。它的自在坦然,豐富多面,使紀錄片透出難得的趣味性。」
同志之戀,公開的性取向
說到對女性題材的偏愛,關錦鵬說:「這可能跟我的成長有關。父親在我十幾歲的時候就去世了,母親是一個蠻傳統的家庭主婦,從來沒有做過工。當家庭發生變故後,她必須承擔起雙重責任,在外面要賺錢,回家還要帶孩子。」從那時起,關錦鵬常常在一邊觀察母親所做的一切。從母親身上,他看到了女性的堅韌,成人之後,他在很多優秀女性的身上看到了和母親同樣的特質。從《胭脂扣》到《阮玲玉》到《紅玫瑰白玫瑰》,他的作品始終散發著對女性的尊重和關照──都市的背景,感性的片段。而他個人的性向,成全了他的陰柔細緻的風格。
而男性亦有女性的觸覺,則與他個人的情感取向是分不開的。一九九六年,就在紀錄片《男生女相》的威尼斯影展上,關錦鵬首度公開了自己的同性戀身份。他對一件事物的觀察和反應,眼光是男性的,也是女性的,它們混雜在一起,分不清先後,幾乎是一種本能。
14歲時,關錦鵬看一些武俠電影,其中一個男人可以為另一個男人出生入死、赴湯蹈火的情誼讓他神往,此時他還未明自己的性向。當成年之後他公開承認時,人們有驚訝,但沒有非議。因為當時,已經有許多關於這一主題的小說、戲劇、電影出現,人們也有比較開明的理解。難得的是,在面對各種表情的時候,關錦鵬始終坦然。
關錦鵬和男友威廉 他與男友威廉,因為一個偶然的機會在一起喝酒而認識,開始交往。一個禮拜後,雙方好像互相有了承諾,便住到了一起。這一住,就是十多年。
他與男友威廉,因為一個偶然的機會在一起喝酒而認識,開始交往。一個禮拜後,雙方好像互相有了承諾,便住到了一起。這一住,就是十多年。
很多人都對同性戀的情感非常好奇,不知道它與異性戀相比,到底有什麼不同。關錦鵬很坦率,他說:「基本上我覺得沒有什麼不一樣的。當然具體到某個結果來說,也許有不同。比如說我和我朋友的關係,他覺得我們之間惟一的遺憾就是,沒有我們的孩子。相對於異性戀來講,這就是缺陷。」
他們也想過領養,但是在香港,就算男人跟女人結婚,也要弄一個證明出來說夫妻之間不能生育,才可以有機會去領養,還要經過申請。對同志伴侶來講,根本不可能。
現實中的許多夫妻,維系其感情的紐帶有許多,可能是經濟的,也可能是孩子。但是在關錦鵬的「同志」戀情裡,他和男友之間的感情的維系,起碼孩子是沒有了。他們確實也需要某種調適。這種調適很難說到底是什麼東西,經濟可能是一方面,有可能是相互之間的一種習慣。反正得有個人和你一起吃飯,當那天所有朋友都沒空跟你吃飯的時候,你就回家跟他吃頓飯。那種感覺可能已經彌補了沒有兒女的缺陷。
這樣的「同志」戀情,事實上跟多數夫妻之情一樣,時日久了,就自然地變成了溫情。
關錦鵬已經把他的男友帶入自己的家庭,很多時候威廉跟關錦鵬的兄弟姐妹聊天的時間比他還多,威廉甚至可以跟關錦鵬的母親煲兩個小時的電話粥,他已經變成關錦鵬家庭的一份子。「我常常講他已經是我的家庭成員,我母親好像多了半個兒子,我兄弟姐妹好像多了一個哥哥。」
「同志」身份,使他多了一個思考角度 同時作為同性戀和導演,關錦鵬坦言,在很多感性的事情上,他常常會帶入一些女性的思維去思考,雖然他並沒有直接把自己當作女性,他一直很清楚自己男性的性別。
同時作為同性戀和導演,關錦鵬坦言,在很多感性的事情上,他常常會帶入一些女性的思維去思考,雖然他並沒有直接把自己當作女性,他一直很清楚自己男性的性別。
多一個角度思考,對自己的電影事業確實大有裨益。關錦鵬舉了一個例子,在戲曲中,一些男性反串女角的,反而比女人演得更加傳神生動,這是為什麼?因為男性在觀察或表演時,會將很多女性的東西放大,「大於生活」。所以曾經有人說過這樣的話,其實男人沒有資格來評論男人,更沒有資格來評論女人,反之亦然。那麼誰有這個資格呢?也許只有同性戀者。
事實上,確實有許多同性戀者在藝術領域裡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成就,關錦鵬的解釋也許很有道理:藝術本身就具有戲劇性,有很多矛盾在裡面。你作為男性,但是你自己很多時候可以有女性的敏感,或者女性的觸覺,所以在這過程裡面他已經非常戲劇性了。而人們對藝術的期待,本身就頗具戲劇性。
作為少數群體的一員,關錦鵬承受過非常多的壓力,像《藍宇》中的「捍東」一樣,他也曾痛苦失落過,但是有一天他終於想通了,覺得坦然面對自己的選擇更重要。當他覺得自己應該尊重自己的選擇時,他心頭的重壓消失了。「你自己都不去尊重自己的選擇的話,就不要要求人家會尊重你。」對於他個人來講,他對自己今天的狀態非常坦然,從而在創作上也多了很多的自由。
現代社會已經越來越多元化,這是「同志」關錦鵬深感幸運的,他同時認為每個人都應該去接近甚至走入這個多元的社會,讓自己接受和理解更多的東西,包括同性戀。有人用是否完全將同性戀視為平等,來區分現代世界觀和後現代世界觀,但是人生有時候並不需要太深奧的道理去選擇。就像關錦鵬,當年他摒棄5年的理科學習而從文,從正統的高等教育跨入電影事業,從一個普通男性到做一個被多數人另眼相看的同性戀者,他只是一直跟隨著自己的心靈。
關於《藍宇》:我既是捍東,也曾是藍宇 說到經典的同性戀題材電影,不得不提到關錦鵬導演的《藍宇》。當年,它一舉拿下金馬獎的多項大獎,並且商業上也獲得了一些成功,不僅讓同性戀們感動,也讓很多異性戀也為之落淚。
說到經典的同性戀題材電影,不得不提到關錦鵬導演的《藍宇》。當年,它一舉拿下金馬獎的多項大獎,並且商業上也獲得了一些成功,不僅讓同性戀們感動,也讓很多異性戀也為之落淚。
《藍宇》改編自小說《北京故事》,小說一開始描寫了這兩個男人性愛的那種場面,非常露骨,它引起廣泛的討論也正就是這個東西。但是從小說改編到電影,關錦鵬選擇儘量把這些拋棄掉,而集中在兩個男主角跨度十年的感情上面去。他聯想到自身的感情經驗,跟男友在一起的十多個年頭,在不同的階段:「我既是撼東,也曾是藍宇」。有最熾熱的時刻,有清淡的生活,也有吵架瀕臨分手的一刻。有受到家人的壓力,朋友的壓力,甚至自己本身作為一個同性戀者的壓力。正因為這樣的感情他本人經歷過,深有體會,所以拍攝過程中,他並沒有太在意劇中的兩個男主角是同性戀還是異性戀,而著重於講述這段十年離離合合的感情關係,把它還原到人類感情上面悲歡離合最基本的一些元素上面去。
「我作為一個同性戀者,走過了十幾年來,我現在跟我朋友處在一起已經十二年了,有很多東西正正在我這生活的經驗裡面,完全可以在這兩個角色的感情關係裡面看得出來。」他說。
張愛玲,每年都要讀一讀 關錦鵬高中開始看張愛玲,此前看的是瓊瑤:「張愛玲是可以在家裡乖乖地看,瓊瑤則是上課時,放在台子底下偷偷看。」 至今,他還記得那些名字如《窗外》、《船》,「那時候,年紀還小,瓊瑤的小說還是煽情的!」
關錦鵬高中開始看張愛玲,此前看的是瓊瑤:「張愛玲是可以在家裡乖乖地看,瓊瑤則是上課時,放在台子底下偷偷看。」 至今,他還記得那些名字如《窗外》、《船》,「那時候,年紀還小,瓊瑤的小說還是煽情的!」
待到長大,才發現張愛玲是每年都要拿出來讀一讀的;瓊瑤則是過了那段年月,再也不曾翻開過。
他最愛的一篇,不是《紅玫瑰與白玫瑰》,而是《沉香屑──第一爐香》──葛薇龍的故事。「張愛玲說過一句話,人要厚道,才懂得尖酸。這個故事體現得最淋漓盡致。」關錦鵬笑著回轉到自己身上:「我有時候挺尖酸的,不過我沒到達她的厚道。張愛玲因為看透很多東西,才懂得刻薄別人。況且,張愛玲對自己也一樣尖酸。」
有人曾說關錦鵬太敬畏張愛玲了,以至於在《紅玫瑰與白玫瑰》裡老老實實用張愛玲的原話作畫面間隔。他卻說:「張愛玲的話,常常後兩句是前兩句的反諷。她有她的多層次,不是單一的──內心狀態很難用,影像上不好呈現。我覺得這樣比較忠於張愛玲。」
說起當年拍《紅玫瑰與白玫瑰》,也是一樁趣聞:「投資人一看,以為是兩個女人的故事,就想到了我。他搞錯了,覺得我擅長拍女性。其實,這哪裡是關於兩個女人的故事呀,明明是關於佟振保的故事。」
新曝光的《小團圓》,關錦鵬看了,喜歡得不得了:「比《色,戒》更大膽,更女性情色文學。」問他想不想拍,關錦鵬搖頭。不是不想,是怕投資太大。而且它是更厲害的女性「情色」文學。如果顧忌這個顧忌那個,搞到最後什麼都不能拍,寧可不拍。
但,這個誘惑太大,話一出口就被他自己駁回:「如果有人拿著投資,買來劇本,找我放手拍──我一定會答應下來。」
《長恨歌》,頗有些恨 20年前的《胭脂扣》,讓他輝煌一時,4年前的《長恨歌》,卻讓他頗為落寞。
20年前的《胭脂扣》,讓他輝煌一時,4年前的《長恨歌》,卻讓他頗為落寞。
票房上看,《長恨歌》是失利的,一些專業人士也覺得拍得不是很成功。
回想起當年洪水般的負面評論,關錦鵬說:「要說當時一點打擊都沒有……我自己很清楚,《長恨歌》對我的殺傷力。」長長的停頓之後,關錦鵬終於用最簡單、最快速、最平靜的語速總結:「當時找資金啊、我自己的狀態啊都受到一定的影響。但,我覺得事情發生了,總要去面對吧。我沒有刻意掉頭搞一個商業的劇本,挽回票房。我沒有這麼做。」
此後,他又嘗試了很多事情,拍電視劇,做舞台劇。嘗試後才知自己終究屬於銀幕:「電視劇以後再也不做了,太累,比拍電影累。常常為了遷就劇情,把人物的性格都前後扭曲了。我不願意這樣。」
2009年6月26日,關錦鵬新片《用心跳》宣佈開機。這次《用心跳》的演員,來自上海戲劇學院和上海音樂學院。「他們有年輕的騷動,這讓我覺得新鮮。我自己都好久沒有穿藍牛仔褲、白球鞋,我買了兩雙。其實,我的心態就一直是年輕的!」當18個年輕人跳著舞上場時,大家都覺得這次故事不那麼「關錦鵬」。他堅信,這次的選擇是對的:「我沒有刻意迴避拍老上海。《長恨歌》以後,我再去拍一個老上海的題材,大家的疑問更大。《用心跳》的資源當然沒有《長恨歌》的資源大。穿越到1930年代的上海只是個小點子,大家關心的應該是我怎麼拍2009年的上海。」
還有一部新片,他正在接觸中,題材很大膽,關於性別越界和易裝。「他們找我,覺得我能把握這種題材,也許和我的取向也有關吧。」關錦鵬的聲音不大,但很是坦率。
關錦鵬的生活和大多數人很不同,但是看他的電影,我們總能在細微的瞬間與他共鳴,就像有一道輕輕架起的浮橋,搭建在人與社會、少數人與多數人之間。
本文原載:明宗網 2009-09-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