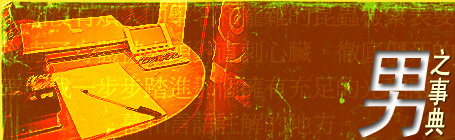我喜欢写,更胜于说。喜欢笔尖划过纸张表面时发出的沙沙声,喜欢不必刻意寻找对象面对面丶即能畅所欲言的感觉,更喜欢那种,当教授口沫横飞着连篇理论时,我只身一人遁进另一个国度,连一句交代也不需要的逃逸快感。
那里没有烦人的学名和庞杂的昆虫检索表要背,更没有一只只挺直了身体被大头针直刺心脏,彻底僵死的蝴蝶和蟑螂。一股巨大而神秘的洪流,牵引我一步步踏进那个拥有充足的光和雨,繁花盛放且从不需要字幕和言语注解的地方。
我自不量力地提起笔,想把那里的一景一物,从墨水里释放出来。我写小说,因为那种可以随心所欲创造角色,并在其间任意切换丶接问对答的感觉,实在是太适合从小就习惯「演」得不亦乐乎的我了。
即使同学总是摇头说「看不懂」,这却是大学时代的我,几乎唯一持续努力过的事。因为写,所以知道自己的层级有多低微,要写的画面明明都在脑里完整齐备了,就差笔力临门一脚。但,任凭脑内澎湃汹涌,思绪顺流而下经过肩膀丶穿过胳膊,来到手指与笔管时已经仅存两滴不到。写了划掉丶改了再涂,最后受不了这吞吞吐吐的折磨,索性整张揉掉。
很气恼。但眼高手低的毛病,一时三刻也改不了。唯一能做的只有留下来丶继续搏斗。因为,忘不了当指上终于出现一串像样的句子丶一场如实呈现的情节,心上乍然开朗的那股无上快感。雀跃,或者说魂灵「归位」,当轻舟已过万重山,回望来路的崎岖和艰难,一声虚弱却饱实的微笑,足抵黄金万两。
此番「文艺青年」乐此不疲的自虐,跟着我走进了职场。而,全然无心且全然意外的,我的第一本书──《男同志网上完全邂逅手册》(开心阳光)在九九年出版。
「邵祺迈」这个名字,便是在那时随口取的。那念起来像是台语脏话的谐音,当然是故意的。写了这么多年的小说,何以第一本正式问世的书竟是工具书,也与小说全无关联?是因不同写作路线而进行的分割,但也像对自己写作轨迹的一次讥嘲。名字里刻意埋进的恶趣味,是要让读者看了就能迅速意会笔调里的不正经,读完甚至笑着啐一声:肖──鸡掰!
我必须承认,那个名叫「邵祺迈」的人,日子过得比我自由且愉快。他可以不计形象的嘻笑怒骂,像是在《欧巴桑养成密技》里,对中年妇女的特殊行径进行一轮彻底讥嘲;他也可以很认真的号召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用一整年时间踏遍全台各地,写完一本有史以来最厚(480页)丶也最完整的中英对照同志旅游指南书《台湾G点100全都录》。
偶尔,他想走走纯情路线,写下《纯男物语》来自爽;生性太爱色情片,又忍不住要把这邪门歪道的雅好和心得,跟同好们分享,一些读过「G片工场」的人以为他是一名既色又怪的糟老头,因为早就力不从心丶只能搜集大量G片过干瘾,他听了反而开心得要命。除了这些,他还每天帮《苹果日报》设计一则「填字游戏」,每周发一篇谈美食的「美味内心戏」电子报,到数万读者的信箱。
我和「邵祺迈」,不是依附着同一具躯体而存在吗?何以他会经常性的去到我所不熟悉丶甚至难以理解的地方,也丝毫没有想要停止「到处留情」的迹象?他比起我,更有话想说丶也更敢说,不惜扮丑成蠢妇或糟老头,好把自觉有趣的事,用他自己的语言说出来──坦白说,身为「同业」,我并不特别敬爱他,但我确实是,打从心底羡慕着他的。
如果──我们换用另一种较为俗气的说法──「邵祺迈」是住在我身体里,一部分的我自己,那么透过那些写作尝试,我似也发现了许多自己从未想过能够拥有的面貌。像被附身一样的体验,当我在篇名之下键入「文/邵祺迈」字样的那一刹,就自然而然使用起一种「很不像我」的口吻丶写出一篇篇文字。而那是过去使用着本名的我,从来不曾体会到的。
或许就类似,当你去到Gay bar丶三温暖或公园,会暂时放下父母为你取的名字,换小名丶绰号丶英文名或花名上场,才能让你和旁人都感轻松自在,并顺利与新朋友聊开──那样的心态。那不是刻意的欺瞒或躲藏,而是,当你叫做Alex丶阿力丶小杰的时候,你所使用的语言丶说话的表情和神态,都迥异于在会议桌丶办公室丶和家人的晚饭餐桌等任一个你必须叫做「陈先生」或「黄XX」的场所。而且往往,你喜欢身为Alex丶阿力或小杰时的自己,远远超过那个身分证上的自己──因为自在,我们愿意释放得更深入丶也更多。

这算一种不诚实丶逃避丶或者刻意撒谎?至少,我并不这样想。如果连为自己取个绰号的权力都没有,这所谓的「圈子」,还会有多少令人发指的规则必须遵守?
邵祺迈从来没有想过,会有这么一天,要用一整篇文章来交代「邵祺迈」三个字的来龙去脉,更没有料到要把从前所做过写过丶意义于我早已如浮云的事情和作品,一一翻找丶并且罗列出来──看起来还颇有自吹自擂的嫌疑。
是这样的。报上登出一则书评,对一本新近问世的文集多所贬抑和批评(避免误会,且容我先说一句:它言重了,这本书真的没有太差!),而作者是一位公开出柜的年轻男作家。
一位匿名读者留言说:作为一个小有名气的作家,敢这样暴露自己,比起那些「符合」同志运动精神的大胆小说描写丶却只敢躲在虚拟文体后面,甚至根本就用的是笔名的一些作者,真不知道谁比谁有勇气一点,谁比谁更符合同志运动精神,谁比谁要承受更多的异性恋社会压力?
我登时骇然:什么时候单纯一个拿笔写字的人丶区区一只用来发表的笔名,都被拉扯上了「同志运动精神」?
以本名或笔名发表,又何时成为判别作品高下的准则?张爱玲丶白先勇丶朱天文,这几位我无比敬爱并且杰出的「本名作家」,他们的作品毫无疑问已成经典,但柏杨丶三毛丶琼瑶丶金庸丶倪匡……数不完的「笔名作家」,又有谁能说他们因为用的不是本名,所以作品只能屈于二流?
何以这位读者从不对上述这群作家进行本名与笔名的质疑和批判,却在面对具备同志身份的作者(群)时,就忙不迭板起了脸孔指控:使用笔名的人都是「躲在虚拟文体背后」丶不愿承受压力丶不符合同运精神?
当每一个握起笔杆的同志,以无比真诚的心情,在面对丶剖析丶书写丶纪录着我们各自的成长经验丶恋爱酸楚丶和族群观点时,仅仅因为我们使用的是一个和身分证上不同的名字,这些努力便等同于空白,不再值得一提或尊重?又,因为用了笔名,这些文章就注定无法唤起共鸣丶也等同于虚假的「次级品」?
──那么,这位留言的读者,你又何以甘于「匿名」的身分,不愿留下你所珍而重之的名姓,好让我们──这群习于使用「伪名」的作者──看看:什么是真正的「有勇气」丶「承受异性恋社会压力」和「符合同志运动精神」?
对「自家人」(如果我们算是的话)的刻薄攻讦,永远比对外人来得火力猛烈。是,我是同志,但我同时拥有更多其他的身份。身份最多的时候,我同时是:丈夫丶男友丶儿子丶室友丶编剧丶研究所学生丶专栏作者丶书籍主编丶出版行销…….而光是在写作类型上,除了Fridae的两个专栏,我同时在写的还有:书评丶美食散文丶旅游和美食指南丶人物专访丶纸上游戏丶心理测验和电影剧本,还有一些突如其来的散杂稿约。我对我的同志身份引以为傲,却百分之两万不愿同意:我所写出的每一个字丶每一篇每一部作品,都必须具备所谓「承受异性恋社会压力」的「同志运动精神」。
身为一介渺小如草丶连「作家」这种大帽子也终身不愿戴上的卑微写作者,我想做的事只有「写」──把我所见丶所想的,化成文字说出来。用哪个名字发表,从来就不该是「写作」本身该算计的事。该担忧的只有:写出来的作品,能不能连自己都喜欢。
请勿把「同志运动精神」窄化到「名字」的身上,也请不要企图高估了每一个拿笔的人。选择用什么名字,是作者自己的权力,个中理由也成千上百,但「使用本名」等于「出柜」等于「勇敢」,「使用笔名」等于「不敢出柜」等于「懦弱」和「躲藏」?虽然,写出你现在所读的这篇文章的作者,确曾站在同志运动队伍最前头的宣传车上,手持麦克风带领数以千计的抗议人潮向警察呼口号,但同志运动并不比较「谁做得多」丶又是「谁做得好」。漫长的平权路,携手同行都来不及,又岂有时间在那里暗中计算:谁又比谁更勇敢?
让作品自己说话。能引发感动和共鸣的,就是好文章。而当作品完成,那种无法言喻的快乐,则是令我愿意一直写下去的最大动力。
此时此刻的我,选择了乖乖坐在桌前,把文章写好。因为这是「本分」,我该做丶也最想做的事。不管发表时选用的是哪个名字,它都会一如我对自己同志身份的看待:始终真诚,并继续一往情深。
PS.篇名「?⒚?刮?瘴暮鹤郑?饨?讣倜?埂?br />
作者邵祺迈交友档案 欢迎指教分享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