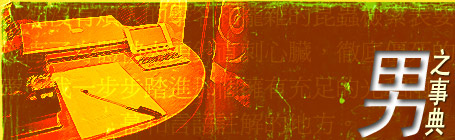我喜歡寫,更勝於說。喜歡筆尖劃過紙張表面時發出的沙沙聲,喜歡不必刻意尋找對象面對面、即能暢所欲言的感覺,更喜歡那種,當教授口沫橫飛著連篇理論時,我隻身一人遁進另一個國度,連一句交代也不需要的逃逸快感。
那裡沒有煩人的學名和龐雜的昆蟲檢索表要背,更沒有一隻隻挺直了身體被大頭針直刺心臟,徹底僵死的蝴蝶和蟑螂。一股巨大而神祕的洪流,牽引我一步步踏進那個擁有充足的光和雨,繁花盛放且從不需要字幕和言語註解的地方。
我自不量力地提起筆,想把那裡的一景一物,從墨水裡釋放出來。我寫小說,因為那種可以隨心所欲創造角色,並在其間任意切換、接問對答的感覺,實在是太適合從小就習慣「演」得不亦樂乎的我了。
即使同學總是搖頭說「看不懂」,這卻是大學時代的我,幾乎唯一持續努力過的事。因為寫,所以知道自己的層級有多低微,要寫的畫面明明都在腦裡完整齊備了,就差筆力臨門一腳。但,任憑腦內澎湃洶湧,思緒順流而下經過肩膀、穿過胳膊,來到手指與筆管時已經僅存兩滴不到。寫了劃掉、改了再塗,最後受不了這吞吞吐吐的折磨,索性整張揉掉。
很氣惱。但眼高手低的毛病,一時三刻也改不了。唯一能做的只有留下來、繼續搏鬥。因為,忘不了當指上終於出現一串像樣的句子、一場如實呈現的情節,心上乍然開朗的那股無上快感。雀躍,或者說魂靈「歸位」,當輕舟已過萬重山,回望來路的崎嶇和艱難,一聲虛弱卻飽實的微笑,足抵黃金萬兩。
此番「文藝青年」樂此不疲的自虐,跟著我走進了職場。而,全然無心且全然意外的,我的第一本書──《男同志網上完全邂逅手冊》(開心陽光)在九九年出版。
「邵祺邁」這個名字,便是在那時隨口取的。那念起來像是台語髒話的諧音,當然是故意的。寫了這麼多年的小說,何以第一本正式問世的書竟是工具書,也與小說全無關聯?是因不同寫作路線而進行的分割,但也像對自己寫作軌跡的一次譏嘲。名字裡刻意埋進的惡趣味,是要讓讀者看了就能迅速意會筆調裡的不正經,讀完甚至笑著啐一聲:肖──雞掰!
我必須承認,那個名叫「邵祺邁」的人,日子過得比我自由且愉快。他可以不計形象的嘻笑怒罵,像是在《歐巴桑養成密技》裡,對中年婦女的特殊行徑進行一輪徹底譏嘲;他也可以很認真的號召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用一整年時間踏遍全台各地,寫完一本有史以來最厚(480頁)、也最完整的中英對照同志旅遊指南書《台灣G點100全都錄》。
偶爾,他想走走純情路線,寫下《純男物語》來自爽;生性太愛色情片,又忍不住要把這邪門歪道的雅好和心得,跟同好們分享,一些讀過「G片工場」的人以為他是一名既色又怪的糟老頭,因為早就力不從心、只能蒐集大量G片過乾癮,他聽了反而開心得要命。除了這些,他還每天幫《蘋果日報》設計一則「填字遊戲」,每週發一篇談美食的「美味內心戲」電子報,到數萬讀者的信箱。
我和「邵祺邁」,不是依附著同一具軀體而存在嗎?何以他會經常性的去到我所不熟悉、甚至難以理解的地方,也絲毫沒有想要停止「到處留情」的跡象?他比起我,更有話想說、也更敢說,不惜扮醜成蠢婦或糟老頭,好把自覺有趣的事,用他自己的語言說出來──坦白說,身為「同業」,我並不特別敬愛他,但我確實是,打從心底羨慕著他的。
如果──我們換用另一種較為俗氣的說法──「邵祺邁」是住在我身體裡,一部分的我自己,那麼透過那些寫作嘗試,我似也發現了許 多自己從未想過能夠擁有的面貌。像被附身一樣的體驗,當我在篇名之下鍵入「文/邵祺邁」字樣的那一剎,就自然而然使用起一種「很不像我」的口吻、寫出一篇篇文字。而那是過去使用著本名的我,從來不曾體會到的。
或許 就類似,當你去到Gay bar、三溫暖或公園,會暫時放下父母為你取的名字,換小名、綽號、英文名或花名上場,才能讓你和旁人都感輕鬆自在,並順利與新朋友聊開──那樣的心態。那不是刻意的欺瞞或躲藏,而是,當你叫做Alex、阿力、小杰的時候,你所使用的語言、說話的表情和神態,都迥異於在會議桌、辦公室、和家人的晚飯餐 桌等任一個你必須叫做「陳先生」或「黃XX」的場所。而且往往,你喜歡身為Alex、阿力或小杰時的自己,遠遠超過那個身分證上的自己──因為自在,我們願意釋放得更深入、也更多。

這算一種不誠實、逃避、或者刻意撒謊?至少,我並不這樣想。如果連為自己取個綽號的權力都沒有,這所謂的「圈子」,還會有多少令人髮指的規則必須遵守?
邵祺邁從來沒有想過,會有這麼一天,要用一整篇文章來交代「邵祺邁」三個字的來龍去脈,更沒有料到要把從前所做過寫過、意義於我早已如浮雲的事情和作品,一一翻找、並且羅列出來──看起來還頗有自吹自擂的嫌疑。
是這樣的。報上登出一則書評,對一本新近問世的文集多所貶抑和批評(避免誤會,且容我先說一句:它言重了,這本書真的沒有太差!),而作者是一位公開出櫃的年輕男作家。
一位匿名讀者留言說:作為一個小有名氣的作家,敢這樣暴露自己,比起那些「符合」同志運動精神的大膽小說描寫、卻只敢躲在虛擬文體後面,甚至根本就用的是筆名的一些作者,真不知道誰比誰有勇氣一點,誰比誰更符合同志運動精神,誰比誰要承受更多的異性戀社會壓力?
我登時駭然:什麼時候單純一個拿筆寫字的人、區區一只用來發表的筆名,都被拉扯上了「同志運動精神」?
以本名或筆名發表,又何時成為判別作品高下的準則?張愛玲、白先勇、朱天文,這幾位我無比敬愛並且傑出的「本名作家」,他們的作品毫無疑問已成經典,但柏楊、三毛、瓊瑤、金庸、倪匡……數不完的「筆名作家」,又有誰能說他們因為用的不是本名,所以作品只能屈於二流?
何以這位讀者從不對上述這群作家進行本名與筆名的質疑和批判,卻在面對具備同志身份的作者(群)時,就忙不迭板起了臉孔指控:使用筆名的人都是「躲在虛擬文體背後」、不願承受壓力、不符合同運精神?
當每一個握起筆桿的同志,以無比真誠的心情,在面對、剖析、書寫、紀錄著我們各自的成長經驗、戀愛酸楚、和族群觀點時,僅僅因為我們使用的是一個和身分證上不同的名字,這些努力便等同於空白,不再值得一提或尊重?又,因為用了筆名,這些文章就註定無法喚起共鳴、也等同於虛假的「次級品」?
──那麼,這位留言的讀者,你又何以甘於「匿名」的身分,不願留下你所珍而重之的名姓,好讓我們──這群習於使用「偽名」的作者──看看:什麼是真正的「有勇氣」、「承受異性戀社會壓力」和「符合同志運動精神」?
對「自家人」(如果我們算是的話)的刻薄攻訐,永遠比對外人來得火力猛烈。是,我是同志,但我同時擁有更多其他的身份。身份最多的時候,我同時是:丈夫、男友、兒子、室友、編劇、研究所學生、專欄作者、書籍主編、出版行銷…….而光是在寫作類型上,除了Fridae的兩個專欄,我同時在寫的還有:書評、美食散文、旅遊和美食指南、人物專訪、紙上遊戲、心理測驗和電影劇本,還有一些突如其來的散雜稿約。我對我的同志身份引以為傲,卻百分之兩萬不願同意:我所寫出的每一個字、每一篇每一部作品,都必須具備所謂「承受異性戀社會壓力」的「同志運動精神」。
身為一介渺小如草、連「作家」這種大帽子也終身不願戴上的卑微寫作者,我想做的事只有「寫」──把我所見、所想的,化成文字說出來。用哪個名字發表,從來就不該是「寫作」本身該算計的事。該擔憂的只有:寫出來的作品,能不能連自己都喜歡。
請勿把「同志運動精神」窄化到「名字」的身上,也請不要企圖高估了每一個拿筆的人。選擇用什麼名字,是作者自己的權力,箇中理由也成千上百,但「使用本名」等於「出櫃」等於「勇敢」,「使用筆名」等於「不敢出櫃」等於「懦弱」和「躲藏」?雖然,寫出你現在所讀的這篇文章的作者,確曾站在同志運動隊伍最前頭的宣傳車上,手持麥克風帶領數以千計的抗議人潮向警察呼口號,但同志運動並不比較「誰做得多」、又是「誰做得好」。漫長的平權路,攜手同行都來不及,又豈有時間在那裡暗中計算:誰又比誰更勇敢?
讓作品自己說話。能引發感動和共鳴的,就是好文章。而當作品完成,那種無法言喻的快樂,則是令我願意一直寫下去的最大動力。
此時此刻的我,選擇了乖乖坐在桌前,把文章寫好。因為這是「本分」,我該做、也最想做的事。不管發表時選用的是哪個名字,它都會一如我對自己同志身份的看待:始終真誠,並繼續一往情深。
PS.篇名「仮名」為日文漢字,意近「假名」。
作者邵祺邁交友檔案 歡迎指教分享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