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蠢蠢欲动,不外是想接触男色、掉到金龟婿。
这样,他逐家挨户,开始掌握了市价、抽佣之分、按摩手艺、特别服务……懵懂的他还同时在两家按摩中心留下了玉照,供顾客「叫外卖」。
那已是若干年前的事,后来因手上直销的工作过累、两个月内作不上十单生意的按摩业绩,在最后一次与老板闹翻后,也就不干了。
咄咄逼人是他不圆滑的表现,似乎注定,他是吃记者饭碗的。
虽有了按摩小生的经验,不过到三温暖去钓人,他在去年的圣诞节前,都还算是初哥。
第一次到三温暖,是他给自己的二十五岁生日礼物,原本还打算告知天下好友,他是同志。
后来圈内的人都劝奉他别太冲动,身边的好友可能还没准备好这事实。
公开出柜一事后来草草了事,他心底暗称,「好险!」
他还借故卖醉要到新开张的三温暖去,结果没上套,任由他人骑在身上,弄得胯下酸痛。
他还记得在首次同志聚会上质问了在场的几位酷儿,到底怎样才算是开放的同志。
向家人出柜?搞性爱三人组?易装秀?不抗拒娘腔作势?穿丁字内裤?或戴耳环招摇过市?
表面上看来道貌岸然的他,在好友相会之间,不时暗示每个人其实都有自个儿黑暗的一面。
他虽接受了家庭暴力的事实,不过当他在过节时与父亲殴斗起来,他彻底地感到痛快,将多年来的怨恨宣泄如海。
那是第一次他深深察觉,原来自己已独撑一面。

他一再强调自己多矜持自爱,却也一再犯罪,浏览色情网站无数,在暗处自摸呻吟。
堕落,他总是这样回答朋友「最近可好?」的寒暄。
若要数落自己,他要清单可是「一匹布长」:十二岁从厕所的隙缝窥看男人沐浴;十四岁在后巷游说「白粉友」口交;十六岁在公众泳池引诱欧巴桑进行肛交;十八岁在公园相人性交;二十岁搞网上性爱;二十二岁当按摩小生;二十四岁参加了性爱派对。
这些都是不可告人的秘密,就算是对男友,他也矢口不提,话题总会绕著几岁发现自己的性取向、与身边男子不同的嗜好、第一次到同志酒吧的经验、欣赏哪一位同道中人……
他还以为爱是越做越爱,结果当对方说,让我听听你的心跳时,他才讶然自己是个无法耕耘感情的人。
好多时候他觉得记者这个身份,在同志圈子当中,是相当尴尬的一件事。
不是担忧对方的反应过度,避嫌交流同志生活;就是自己多余的猜疑,怕来日公众形象毁于一旦。
虽然撰写爱滋题材或为同志平反刻板印象,在媒体大奖上属讨好性质,他故然避重就轻,不去着手这类的专题报道,只写些性别模糊的情欲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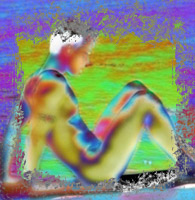
虽在家搁著几片有同志色彩的电影集,他却笑言是为写影评之用,叫家人要开放些,别为这阴阳一体的希腊神话,闹得心惶惶。
虽也在反爱滋非营利组织凑上一角,他并没就职业上的优势而积极扮演教育群众的角色。
对最近院方的Rapid Test Kit检验爱滋设备,政府在推广这健康宣传运动上嫌有怠慢,他大可乔装上门,监督整个求医过程,向有关当局施压。
可是他并没热血澎湃地回应。
较之前李安《断背山》走俏,同事之间相传「断背」笑话,他避开为之,求明哲保身,连低腰牛仔裤也丢到旧皮匣子去。
他对同志走向街头示威,也颇有歧见,咕哝这是在自家干的事,无需张扬争取权益。
他还认为扫黄队逮到同志「摇头」,媒体大幅度渲染,是咎由自取。
这些话,他连自己听起来,都心虚万分。
他明白两男出现在宾馆或三温暖,赤裸上身并不能证明进行「违反自然性行为」或鸡奸,甚至有权反告当权者侵犯私人空间隐私云云……他还是静静承受下来,木然地剪下这个报道,打算,贴在粉红三角组织中心的布告板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