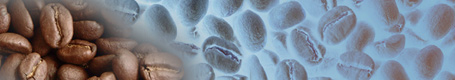扔?我作势把他扛到肩上,要往窗外抛,他哀哀求饶,又笑得喘不过气来。你不是要我扔?
这些年几度搬家,连衣服书籍都能丢下了,这把咖啡糖却没想过不随身带着。
那是一九九六年冬天,我在「公司」遇见了他。
那晚好冷,呼出的气体在稀薄路灯下化成一团团白烟倏即消散,他却穿着一条短裤,两条腿在不听话地打着颤,他的一双细细的眼睛与我对望,朋友鼓动我上前攀谈,好犹豫,但还是踅到了他身边,问,你不冷吗?他回说好冷啊你们台湾。
我意识到他不是本地人,他试着简单交代,破碎的中文却使得他的身世也显得破碎:祖父一辈从金门移民印尼,他的父亲在成年后曾试图回到金门,终究与他想像中的家乡落差悬殊,再度回印尼,结婚,生下了我眼前的他;他来台湾是为了学中文,我好不要脸地说,学中文啊,找我就好了。他嘻嘻傻笑,说自己上课会打瞌睡,唱歌学中文最有效。
他白天上课,课余在博爱路巷子里的旅馆打工,下班都在午夜,我们的约会便从午夜开始;那年冬天很冷,我围着一条围巾带着另一条,骑摩托车到他住宿的巷口等他,帮他将围巾系上,四处晃荡去。
叽叽喳喳地他好爱说话,一会儿在我的右耳边一会儿又在左耳,我左左右右地偏着脑袋去捕捉他瞬间便散逸在风中的声音,有时假装听不清楚,啊什么啊你说什么再说一遍,他越凑越近,终于来到我的势力范围,我瞬地转过头去,在他脸颊上轻轻一啄,好得意。他大叫不行不行,这在我们国家会被抓的。
印尼排华,又是戒律森严的回教国家,他是边陲的边陲,双重的流离;难怪他小心保护自己,连宿舍和打工所在都没主动告诉我,而我,就只是等着。
多半时候我们不知要往哪里去。我们到Funky跳舞吧,他想了想,摇摇头;那我们上阳明山看夜景,他又想了想,又摇摇头;那你想去哪里呢?他嗫嗫嚅嚅语气好委屈:我不知道。于是我们穿戴着夜色,一条街骑过一条街,看着灯火黯了下去又有几盏亮了起来。
我们的关系也像这样,我们进一步交往吧,我说;他嗯嗯地想着,可是,可是我就要回印尼去了;我说,不要去管未来了,就是现在,要不,我们退一步,否则我很痛苦。他也不愿意。他在后座紧紧抱着我,取暖一般,我车子骑得飞快,沉没在沉默里,他唱起歌来了,摊开你的掌心/让我看看你/玄之又玄的秘密/看看里面是不是真的有我有你,就这样我们不进不退,徘徊在冷冷的冬天的台北街头,徘徊在掌心里的感情线与理智线之间,进退都有说不的理由。
春节过后他就要回印尼了。
放年假前我断然把工作给辞了,因为一些不愉快,同时将家用电话换了号码,却在同时间,他也搬离了宿舍,我打电话过去,一个尖锐的女高音重复说着,你拨的是空号,请查明后再拨,你拨的是──同在一座城市里,我们竟就这样断了联络,这是一个九点半档俗滥至极的桥段,却把我抓去当了主角。

我打电话到印尼驻台办事处丶印尼观光局等机构,又到北部几所设有语言中心的学校询问,他们查不到学生资料,但答应将我的寻人启事交给印尼学生组织,回音很快到来,都说没有,没有你要找的人很抱歉喔,也到博爱路去一家旅馆问过一家旅馆,或是还不太熟练地上网登录找人,没有,没有,没有,一个曾经在我耳边讲话唱歌伊伊牙牙说着我捉弄他的「杨丽花发明非挥发性化学花卉肥料」的人,竟就像我虚构的人物,Shift压住后用滑鼠圈出一个反白区,Delete按下,从此消失。
在他预计回印尼当天,我还是去送了他,隔着玻璃窗,我望着一架架飞机逐渐驶离视线。他就在某一个机舱里。
从此我留心印尼的消息,好像我在一个个统计数字里也可以分辨出他所占有的那个独特位置,并用想像使他充满精神。
然而这几年来出现于报端的,多半是灾难新闻,九七年霾害,九八年年中大规模排华丶年底两场空难,○一年?Q里岛爆炸,○四年地震加上海啸肆虐,少则数百多则数十上百万人伤亡,好神经质地我检阅 着一张又一张图片上的人物。你现在三十初渡了,鼻子尖尖眼睛细细和薄薄的嘴唇这些都不会改变;但你变胖了吗?一定是的,唇上蓄短髭了没?那是你所以为的性感符码,像克拉克·盖博;你仍戴着我送你的那个白金手环吗?一如我仍保留着你放在我家的咖啡糖;你在找我吗?你知道我在找你吗?如果你知道我在找你,为什么你不来找我?喔,一定是,一定是你没有我的联络方式了,我这就给你,我的e-mail是──我的手机是──现在我们都用手机了,我的地址是──
伊听着听着,唰地一下眼眶便湿润了,我抱抱他,伊瞬间咧嘴大笑,你被骗了,可恶,你心里原来有别人,改天趁你不在,我代你丢了这些糖果。你敢,我捏捏伊的脸颊,你啊爱哭鬼小心眼。可不是吗,一个假日清晨伊生闷气,我问了半天伊才说,昨晚你怎么背着我睡,以前都是面对面的。
伊不怀好意地说,那是阴谋,一定是阴谋,不这样你不可能记他这样久;伊又认真问我,以后你会不会也像记住他一样记住我?我摩摩他的脑袋瓜,说一声傻蛋。
咖啡糖有保存期限,傻蛋,我真的不知道记忆有没有,也许它像传真纸一样,慢慢地也将褪去了颜色。走吧,傻蛋,我们吃饭去吧,我听到你的肚子饿得咕咕叫了。
本文收录于王盛弘著《关键字:台北》(2008年,台北马可孛罗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