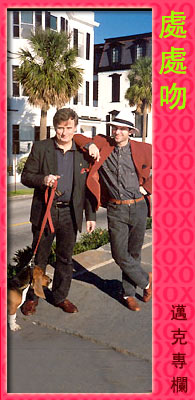
一封生還者和告別者合作的遺書,為他們共處的時間留下見證,加上背景耳熟能詳,才讀了幾句我的眼睛已經濕了。他們幸運,不僅僅相濡以沫不離不棄,最後的時光還要在一個這麼美麗的城市渡過。
赴約不趕時間,路過不介意進去東摸摸西摸摸,也曾經找到有趣的絕版書,但那股灰塵的味道令人不愉快,從不久留。打開艾文韋特(Edmund White)的《我們的巴黎》(Our Paris),第一幅插圖居然是變成黑白線條的店面,真措手不及:像遇到多年不見的點頭之交,沒想到他在別人的世界居然舉足輕重。
書名明明以複數包攬城市,我只提韋特,實在該打。「我們」的共同享有者叫尤柏索蘭(Hubert Sorin),負職繪圖,是當年與韋特雙宿雙棲的男友,兩人住在《蒙娜讀書》五樓。九四年書出版前幾個月,索蘭因愛滋病逝世,死時不過三十二歲。韋特的前言開宗明義:「我許 多患愛滋的朋友,都希望寫一本書或者做點其他藝術品,作為他們於世上及光陰中存活過的慶賀或紀念。」
一封生還者和告別者合作的遺書,為他們共處的時間留下見證,加上背景耳熟能詳,才讀了幾句我的眼睛已經濕了。
他們幸運,不僅僅相濡以沫不離不棄,最後的時光還要在一個這麼美麗的城市渡過。他們的巴黎,其實只是尋常門巷,日子也是開門七件事的日子,然而字裏行間鋪墊着依依不捨,以演述《一千零一夜》的迷信,企圖令聽得失神的死亡使者忘記執行任務。
如果我說讀這本書我的反應是羨慕,請別誤會夾雜任何酸溜溜。十二年過去了,今天愛滋不再被視為絕症,但是我想,某些情懷也隨着時間走了樣……對,我們永遠回不去了。

遇上了,好奇使眼睛發亮,一個微笑,咖啡座摸杯底,去對方喜歡的餐 館晚飯,地鐵站吻別,明天,明天,明天。
遇上了,好奇使眼睛發亮,一個微笑,咖啡座摸杯底,去對方喜歡的餐 館晚飯,地鐵站吻別,明天,明天,明天。
然後故事完結,故事總要完結的,塞納河的水依同一個方向緩緩淌過,遲到的巴士還是遲到,由右岸過橋走向左岸,艾菲爾鐵塔流閃着金光。
他們的活動範圍以第一區為主,搬進住所時周遭沙塵滾滾,門前掘建地下停車場,角落的建築物被改裝成瑪莎百貨。
九六九七年間,有一段時間我必須每日準備二人用早午晚餐 ,技窮之際,不辭山長水遠去瑪莎地窖超級市場購買盒裝熟食,有一款意式磨菇焗飯,吃得特別多。早兩年生意欠佳結業,現在變成西班牙連鎖服裝店Zara,幸好我也不再有籌劃三餐 的煩惱。
算一算,當時索蘭已經過世,韋特大概也搬走了,《我們的巴黎》靜靜坐在書店等候我,包括前言收稍的這個句子:「我也愛他,以我冷漠、節制、迷亂的方式。我希望能令他活得越久越好。這本書讓我們等待結束時有了寄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