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就曾經被這種人騷擾過!」最後他又鄭重追加了一句。
三十好幾快四十的人還這樣被當小孩子警告,面子似乎有點掛不住,「阿尼會是這種怪胎嗎?」我陷入懷疑的痛苦──懷疑有一對鹿般純真大眼的、對巴哈瘋狂的阿尼,但更多的是懷疑自己,自己的判斷力。
但之後發生的事不得不讓我懷疑阿尼是否有些腦袋不正常。因為在另一次台灣友人家裡的聚會中,他突然發神經似地當眾高聲宣佈,說他曾經和此次宴會的男主人在十幾年前約會過。當時場面突然安靜了數秒,我直覺空氣溫度陡降至冰點,氣氛十分尷尬,我本能地要拉他坐下並要他立刻閉嘴,誰知阿尼一派理直氣壯、繼續振振有辭:「他一定是忘了,他一定忘記了我是誰……」當下頗讓男主人難堪下不了台。
「我從來不認識這個人……更何況,我和誰約會過我自己難道會不知道,輪得到他來提醒?」事後男主人私下向我抱怨。
我於是打定主意,不再邀請阿尼參加我任何朋友的聚會,以免到頭來全波士頓我只剩下阿尼一個朋友。
當我試圖漸漸減少和阿尼見面的次數時,阿尼卻主動出擊了。這回他給我出了新的難題。
「Mark,你知道哪裡可以永久存放一個人的DNA?」有一天他直接打電話到我實驗室。以我對他的了解,我直覺地以為他要我回答:我們實驗室的液態氮箱就可以。我把到嘴邊的話又吞了回去,繞個圈子說:「怎么回事?誰的DNA?」
原來阿尼從小是他祖母帶大的,兩人感情好得不得了。十年前他祖母病逝於麻州綜合醫院(Mass General Hospital),留了一小塊病理組織(照阿尼描述應該是一小塊皮膚)在醫院病理部的冰櫃裡。十年是麻州的法定病理切片保存年限,如今期限已過,阿尼收到一張醫院發出的組織即將銷毀的通知。
「你不知道我祖母是多么一個和藹慈祥的好人,她有尊貴的靈魂……她絕對值得再活一次!」阿尼在電活中的最後一句話讓我幾乎當場昏厥。
原來阿尼不知哪裡來的想法,認為人類將來一定有辦法利用DNA將生命體復原,讓生命不斷再製而得到永生。「而有誰比我祖母更有資格得到永生的?」阿尼將他懷中一張寶貝萬分的和祖母的合照出示給我看,眼神中是綿綿不絕的孺慕和愛戀:「所以我絕對不允許 我祖母的那塊皮膚被銷毀,那是她在世上僅存的DNA。」
我看得出阿尼這回玩真的了。

「但即使我拿回了祖母的皮膚,自己也不會保存,總不能就放在家裡雪櫃的冷凍庫吧!」阿尼說。而我只管澆他冷水:「如果全世界的人都和你一樣,那地球早已人滿為患、萬刼不複了。你這樣是在做上帝做的事情你知不知道?」
見我一副無心幫忙的樣子,阿尼更使出渾身解數,實驗大樓四層樓上上下下幾乎都有人接過他的電話。更要命的有一次我在實驗室門口撞見阿尼,天啊,他正和我的「頭家」(實驗室的指導教授)嘻嘻哈哈聊得正起勁呢!
事後我打電話警告他:「阿尼,你這樣做太過份了!你給我離我頭家遠一點!」
「為什麼?我們聊得很愉快啊!」阿尼還是那副永遠滿不在乎的口氣。
還好事情轟轟烈烈進行了快兩個月,似乎有了轉機。醫院方面態度似乎有了軟化,阿尼祖母的皮膚得以繼續保存。是否阿尼的律師發揮了作用就不得而知了。而一旦阿尼不提此事,我也立刻絕口不提,免得再橫生枝節,憑添困擾。
當兩千年的春天來到時,我在哈佛的學業也將近尾聲了。實驗室頭家對我誘之以綠卡,見我不為所動後,也不再留我。而波士頓地區朋友圈中,真正因為我要回台而心急如焚、急得跳腳的,赫然只有阿尼。
「你真的要回台灣了嗎?」阿尼眨著他鹿一般的大眼睛。
「是啊,我們頭家又不留我。」我隨口編了個理由。
「什麼?像你這么優秀的研究人才,你們頭家不要你,別的實驗室一定會要!」阿尼氣忿忿地說。之後他要走了一份我的履歷。
「你想干什麼?」我問。
「你就會知道。」阿尼神祕地說。

「阿尼,你這是在干什麼?」我急起來想阻止他:「這不會有用的……」
「誰說的?」阿尼一臉的得意:「我看MIT的研究生畢業後都是這么做的……」
之後阿尼真的就把他精心印製的我的「求職廣告」,在MIT和哈佛校園裡所有的佈告欄到處張貼。我無力阻止,也只有任由他去。
只是此時我的去意已堅。當我正忙著賣掉家私、收拾行李時,和阿尼的聯繫也漸漸少了。我不知道他是如何面對我要回台灣的事實,像他這么一個熱誠又單純的老人,單身住在冷酷疏離的美國東岸,一定也是寂寞的。他的瘋癲癡傻固然叫人頭痛,但同時也叫人感動,
畢竟他是我哈佛醫學院三年裡,惟一交到的美國朋友。當我回顧這我一生不再的三年,所有值得回憶的美好片斷,赫然大都有阿尼的影子在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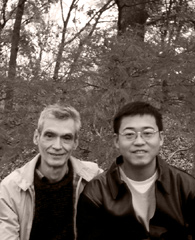
我愛你。阿尼
我心中默念著這在波士頓從未說出口的三個字。
在和他失去連絡的近五年,我曾這樣祈禱:
親愛上帝,如果禰必須選擇一個人類的DNA做為永恆的保存,就請禰選擇阿尼吧!他才是禰天國裡失落的羔羊,落入凡間的天使!
(寫於2006/7/3)
後記:二OO六年一位密蘇里大學文學博士班學生方哲升(Jesse Field)寫了一封伊媚兒來,詢問他以我的作品作為他博士論文主題的可能性,他近期也將在「全球酷兒文學會議」裡提報有關台灣同志詩的書寫現況。於是我們就約在他上課的台大(他來台就讀中文班三個月)附近見了面。哲升是個墨西哥裔的美國青年,之前曾來台灣在故宮當翻譯工作過一年,那時他曾到過我北投家派對,此次算是第二次見面。
相談熟識之後,才發現我們還都同時間在哈佛待過(他那時是碩士班學生),感情更加熟絡。我將當時阿尼寫給我的書信給哲升看,他讀完十分篤定說:從信中的書寫來看,阿尼一定是如他所說的是MIT的退休教授。我一時間啞然。
然而像他這樣一個純真到近乎瘋狂的赤子,他是誰於我已經不再重要了。在返台後遺失他的所有聯絡資料的七年後今日,我只懷疑過自己。
本文原載《印刻文學生活誌》,第49期(2006年12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