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爱都是一样的,就如音乐不应该分什么主流非主流,这不需要。有人觉得我播的音乐怪怪的,但又说不上来哪里怪,但慢慢就会听出它的不同滋味。这跟同性之爱一样,爱情里会发生太多事情。在《房间剧场》里,我提到的很多东西都是在说尊重,尤其是对异己的尊重。跟自己不一样的形状丶思想丶行为丶个性丶打扮,我们是不是可以学习尊重每一个个体?」──万芳
打开《万芳的房间剧场》(以下简称《房间剧场》),屏幕里出现一个陌生女子。这是万芳?素颜长发,宽大长白袍子,状若梦游地自言自语丶唱歌,气场纠结丶脆弱。
时间通道咣当作响,另一头的万芳,模糊得有些隔山看水。那个万芳走在红尘俗世间,一汪澄澈,只一首《新不了情》便唱尽天荒地老暮暮朝朝,再有《猜心》丶《割爱》丶《桂花酿》丶《慢火车》丶《温哥华悲伤一号》,歌里是聚散离合七情六欲。有人说万芳不是在唱歌,简直是在啼血。为情所困的男女,在她的呼吸吐纳里找到出口。
很久没有听见万芳。自《相爱的运气》专辑至今,已7年之久。如今的万芳多了几个不一样的分身。她是音乐节目DJ,商业电台黄金时段,她舒缓却热烈地推介「怪怪的」边缘音乐。她是演员,表演清单上有2部电影丶8部电视连续剧丶14出舞台剧210场累计演出,成绩单里有台湾电视最高奖项金钟奖的最佳女主角和最佳女配角,评委对她的评价是,「看不到表演的痕迹」。她写诗,她主持,她依旧是歌手,只是在用不一样的形式唱歌。
《房间剧场》便是一场无法定义和归类的歌唱。2007年的女歌节上,万芳退进一个私密的房间,用文字丶声音丶肢体和表演概念性地展现自己枝微细节的体验,她讲故事丶在简单的配乐里唱歌丶窝在沙发里发呆丶蹲在地上画蜡笔画丶学小女孩提着裙子蹦蹦跳跳丶模仿女主播大声播报新闻。故事从左手开始。天生的左撇子万芳从小被规定要用右手写字丶吃饭,左手和右手都很沮丧,「是不是跟大家一样就是乖呢?什么是乖呢?为什么花已经不在它的季节开花?为什么爱人会寂寞?我们可不可以不那么伟大」,一连串提问从这「左手意识」开始。以日记丶书信为主轴,万芳选取往日专辑中诗性浓厚的《飞》丶《你的世界》丶《迷 惑森林》丶《知道不知道》等,另有翻唱经典曲目《爱之旅》丶《她沿着沙滩边缘走》和《歌》。
同性爱丶地球变暖丶女性体验,万芳用发问的方式表态,关注「少众的丶异己的丶被忽略的丶不被尊重的」个体,把声音送给那些在人群里沉默不语的「异类」。这些提问,拼凑出一个阶段里完整的万芳。至于答案,她已在这些年的每日生活中一一给出。从下面的对话中,你或许能找到蛛丝马迹。
我知道 说什么都没有意义 / 如果心已经封闭
我知道 时间不断在远离 / 茫然的早晨躺着寂静
我还知道 未来不断在靠近 / 慌乱在思绪满溢的夜里
我知道 假装不会改变事实 / 如果心不是这样
我知道 太用力就容易失去 / 爱情经不起紧握
我还知道 我会哭倒在方向盘上 / 如果一直都太坚强
我不知道 关起房门怎么跳舞
我不知道 音乐响起怎么开口
我不知道 脆弱时候怎么勇敢
关于自己怎么面对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生活可不可以逃避
我不知道 人可不可以消失
我不知道 故事可不可以没有结局
一个人的时候可不可以不勇敢
我不知道 我知道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知道
《知道不知道》
词:万芳 曲:陈小霞
「歌手是上了妆的角色,演员是卸了妆的角色。」
城市画报:过去一年里,有没有什么「第一次」体验?
其实这几年都在尝试新东西,很多个「第一次」。包括持续9年在电台做DJ,做主持人,在演出里头担任诗人,演戏,做演讲者。
城市画报:作为演讲者,讲的内容都有什么?
从1998年开始和台湾佛教慈济基金会有音乐上的合作,之后他们便邀请我去参加活动,譬如在9 • 21大地震丶东南亚海啸丶美国卡特里娜飓风丶四川地震后发起的募款。募款就是募心,希望大家发挥善念气凝聚力量。我在演讲里会分享我跟慈济人的相处,以及我在歌手丶演员等身份中感受到的内容。万芳这个名字有不同的身份,我把所有的角色汇整后再把感受往外传递。我第一次当演员是在1995年,在拍戏的过程中我有很深的感受,觉得歌手是上了妆再跟别人相处的角色,而演员是卸了妆才跟别人相处的一个角色。
城市画报:你信佛吗?
我不是那么完全地懂得宗教。在所有的宗教里头,可能比较偏向佛教。
城市画报:你1995年就毛遂自荐去屏风表演班演舞台剧了,那时你出到第7张专辑,当时算是唱而优则演吗,表演最初吸引你的地方在哪里?
只是单纯有很强烈的动力想去表演,就去做了。当时唱片卖得很好,《割爱》是在我的第一个舞台剧《莎姆雷特》之后出的。在舞台剧的圈子里,他们都叫我万小芳。
城市画报:你扮演的角色迥异。比如盲眼女生丶生病即将离世的妈妈丶排斥艾滋病人的保守者等。你如何接近一个角色?
我在《冷锋过境》里扮演一个罕见疾病肌肉萎缩症患者(编者注:2004年,万芳因《冷锋过境》中的表演获金钟奖最佳女主角),于是会去跟真实的患者相处,甚至把他们拍摄下来。肌肉萎缩症者越靠近心脏的地方越没有力气,怎么梳头丶怎么拿碗拿筷子丶怎么坐椅子丶坐车,这都是我必须要学习的。记得我在演爬楼梯的时候,每爬一段都满身大汗。当时感受很深,演这个戏不过是一下子的辛苦,演完了我就可以好手好脚地恢复原来的日子,可是真正的患者每天24小时都生活在这种辛苦当中。
有时候我会想念我的角色。印象最深的是《长假》,主角是一个到处打散工养家的女人玫瑰,她有一个好赌懒做的老公。有一天玫瑰发现自己生病了,日子不多了,于是她把死亡 当成自己要放的一个长假。她开始教自己的8岁的小孩学煮饭学照顾自己,她写好12封信,托人在每年儿子生日时寄一封给他。这是我们平常生活中时常会碰到的人,一个很平凡普通的妈妈,但她有很饱满的爱去对待家人。演戏的过程里,万芳和玫瑰不断地在我身体里对话,有时候我会进去当玫瑰,有时候我会跳出来当万芳,默默看着玫瑰在做的所有事情。《长假》之后,我很想念她,有时候会想,不知道玫瑰现在哪里,过得怎么样。
「有时候离开是为了看着自己的原型。」 城市画报:从《相爱的运气》至今已经7年了。当时渐渐离开歌坛是有意识丶主动的吗?
城市画报:从《相爱的运气》至今已经7年了。当时渐渐离开歌坛是有意识丶主动的吗?
我其实从来没有离开过歌坛,只是没有出唱片。我也没有离开过唱歌,唱歌对我来说并不是只有当歌手才可以做的事,我从小就唱歌,可以说我现在几岁就唱了几年,歌手只是某一段时间的身份。可是有一段时间我发现,作为歌手的我只能站在舞台上唱歌,反而不能唱给自己听了,这让我蛮伤心的。当你意识到了,就是一个转机。所以我花了一些时间去找回那些最单纯丶最原始的唱歌的快乐。从2002年到现在,我一直都有唱,只是很多演唱形式跟过去不一样,包括《房间剧场》丶《房间唱游》。我并没有刻意离开,只是顺着走。每个人生下来都有他自己的天职,或者说有他要做的功课,在那段时间,我觉得自己好像需要去做些什么事情。
城市画报:当时圈子里有些人觉得你很「怪」。
有人会对我说,唱歌就唱歌嘛,就赚钱嘛,你怎么想那么多?但对我来说唱歌绝对不只是赚钱,所以在沟通的过程中,会有一些很奇妙的东西产生,于是便被认为「怪」。对于他们来说怪的人,可能在另一群人看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在不同的环境,大家用不同的逻辑去看待一个事情。
城市画报:看过那时候你作为艺人上节目玩游戏,你告诉自己「忍一下,像打一针一样过了就好」。当时外界给你的困扰是什么?
它会对我造成困扰的部分在于,偏偏我并没有离开过这个舞台,偏偏我还在这个环境里头。我觉得唱歌不只是唱歌,还要把一些东西传递出去,要达成这一点我必须要有所取舍,包括跟人的接触,要跟一些认为我怪的人接触。这个东西会影响我,有时候我并不那么强壮,我会觉得很沮丧丶很难过丶很生气气丶很胃痛。可那只是一个过程,就像曾经有人跟我说过的一个比喻:一个女人想要小孩,她不能只想要小孩,跳过大着肚子走路,跳过饪振反应,不要怀孕的辛苦,这不可能。每个人都有他的天职,在传递的过程当中一定有些不容易,就是这样而已。因为不容易,所以才要去做。
城市画报:后来怎么慢慢打开「不能唱歌给自己听」的困境?
对我来说,音乐有很多种,而我们从小到大接触到的音乐模样都差不多。整个唱片工业都是一个模式。我从 2000年开始当DJ,可以主动去接触所谓流行音乐以外的不同音乐人,他们打开了我对音乐和生命更多的想像。一次很深刻的接触来自内蒙古歌手乌仁娜。她从小生长在草原,很有音乐天分,她完全不会讲普通话,只会家乡的母语,后来她到上海音乐学院学习,发现所有人进入音乐学院都用一种唱法,只是语言不同而已,所以她非常小心地保护自己来自家乡的歌声,直至现在。后来我和她一起回内蒙古,见到她的家人,看见她资助草原上的孩子们上学。还有客家歌手林生祥,他当年入围金曲奖,有人通知他的时候,他正在帮妈妈养猪。这都很棒,唯有踏实地生活,才能透过音乐丶戏剧等不同的渠道去传递。我觉得唱歌丶演戏丶写诗,都只是传递的管道而已,它们并不是一个王子公主的游戏,我们并不需要被大家崇拜或簇拥,不需要高高在上,我们只是传递者,并没有什么了不起。
城市画报:你的管道源头是什么呢,说说你的每日生活。
我生活很简单,只是多了一些比较细腻的观察吧。整理房间,整理花花草草,自己做早餐,阅读,散步,工作占据了大部分时间。没有工作时喜欢旅行。旅行对我来说是一种借离开对生命所做的一种反刍。早些年,我每次出国旅行,只要超过一个礼拜,就会开始做梦,梦到一些连接我原本状态的事情,那个原本就是我在台湾所熟悉的环境。有时候我看到一些风景飞人文景观丶某些人的样貌,都会连接回我熟悉的环境。其实这就是反刍,内容是在老环境里无法解开的困惑或心结。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你的名字不具有任何意义,你把自己归零,看到自己真实的样貌。有时候离开只是为了看看自己的原型,然后所有重要与不重要的会重新排列。 
「我总在选择-条不是很好走的路。」
城市画报:在《万芳的房间剧场》的DVD开篇,你说「这不是一张快乐的专辑,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太多让人伤心的事」,这近100分钟的画面和声音算是一种疗伤吗?
我做DJ时访问的第一个人是大大树音乐图像的钟适芳,后来我们成为非常好的朋友,其实她根本不知道之前我在唱什么样的歌。有一次她去新加坡看我的演出,她觉得所谓流行音乐的文学化,在我身上完全表露出来了,并不单指文字,而是我所有的演出呈现里都会加入剧场的元素。再后来她邀请我在女歌节上演出,这就是《万芳的房间剧场》的成型。2007年5月我全然投入在《万芳的房间剧场》里,从零变成一部作品,全部要由我自己去发想丶去创造,这个过程非常非常孤独,有时候晚上我会被胃痛痛醒。但是另一个部分的我非常兴奋,因为我们加了很多即兴的东西,我想看看它最后会是什么样子丶什么形状。
《房间剧场》在舞台演出结束以后,要不要出DVD这件事我挣扎了很久。我想这个东西无法是DVD,你必须到现场去感受,它非常私密,它是很多女生的故事,它是很多人的故 事,它是从我出发的小众故事,我当时没有办法再演第3场第4场,它没有办法重复,它就 是生命当下一个很深刻的体验,所有的眼泪所有的诠释都是当下最真实的东西,它不是演来 的。最后有一个力量支持着我,我知道很多听我歌的人,他们的生活不容易,在他们生命当 中,在他们的圈子里头,他们也是小众,他们需要一些发出声音的力量,而《房间剧场》如 果能给他们一些微弱的力量,那么这就是我的心意。
城市画报:《房间剧场》里左手和右手的故事其实意味着对自己的认同,现在你对左手和右手的认同和解了吗?
很多年前,在一次成长团体课程上发现左手意识,我开始去寻找它,长时间的关注点都在左手上,其实就等于忽略了右手的辛苦,它根本没什么力气,但是又要做那么多的事情。我一直觉得自己对不起左手,在筹备《房间剧场》的时候,我发现自己也很想和右手说对不起,这时候就是和解了。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我现在用左手画图,会直接连结到我7岁的时候,右手画出来的线条感觉是经过训练的,而左手画出来的就是7岁小孩会画的东西,很童稚。你可以用用看那只你从来没有使用的手,你可以重新发现自己。
城市画报:「每个艺术家的创作都是在解决一些他童年就存在的疑问」,你怎么看这个观点?
这个想法很有意思哦。人长大了以后,会在某个片刻联结到自己的小时候。当我们回头看自己小时候,会觉得自己原来那么孤单,但其实小时候那一刻的我们并没有那么多的害怕和孤单,只是来来去去,正在发生而已。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次我回首自己的高中生活,看着自己好多年前写的高中日记,一本一本地看,一直哭一直哭,我很想去疼惜那个高中时候的自己。突然有一只手抚摸着我流满眼泪的脸,其实那只手是我想要疼惜高中时候的自己,很有趣的是,后来我发现其实是此时此刻的我需要被疼惜,反而是高中时候的手过来抚摸我。那是好清楚的一个画面。小时候我很怕鬼,总是把自己缩在角落里头,用唱歌来壮胆,度过一整个下午。唱歌是我最深的朋友,是我一个人时候无形的朋友,所以唱歌这个事情我没有办法轻易对待。有时候回想起小时候唱歌的我,她可以给我很多很多的力量。
城市画报:现场的音乐即兴成分有多大?大竹研和谢杰廷的演奏,和你的演唱有时候有些互相抽离。
我们会有一个基本的架构,两个乐器做不到绝对即兴。即兴的部分,譬如每一次我说话的内容会有调整,而大竹研是日本人,或许他听不懂我在说什么,这时候他就需要非常敏感的专注力去感受我的每一次的呼吸,我也要去融合他们的呼吸,三个人在舞台上融为一体。曲子跟曲子之间的每次弹奏都可能不一样。我在舞台上的即兴也包括每一次台下组成的分子不同,观众今天带着一个什么样的情绪和能量进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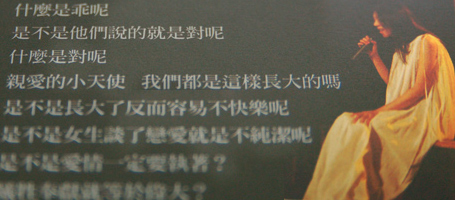
城市画报:《房间剧场》里讲了一个有点残酷的同性爱的故事,随之而来的歌是林夕和黄韵玲写的《迷惑森林》。
所有的爱都是一样的,就如音乐不应该分什么主流非主流,这不需要。我在比较商业的电台,把一些边缘的音乐包装得不着痕迹。我明白很多人的耳朵已经长期习惯了某一种状态,强大的媒体让人觉得音乐就应该是一个样子。有人觉得我播的音乐怪怪的,但又说不上来哪里怪,但慢慢就会听出它的不同滋味。这跟同性之爱一样,爱情里会发生太多事情。
在《房间剧场》里,我提到的很多东西都是在说尊重,尤其是对异己的尊重。跟自己不一样的形状丶思想丶行为丶个性丶打扮,我们是不是可以学习尊重每一个个体?他在这个社群里显得特殊,在另一个社群里其实一点都不特殊,就像有些地方是母系社会,有些地方是父系社会,不过就是这样而已。《房间剧场》是从小众出发的,我本身是左撇子,在这个世界上是小众,我是女性,在社会意义上也是小众,我从我个人出发,延伸到对其他小众的尊重。
城市画报:《房间剧场》里有一个反覆出现的疑问句「可不可以不要」,这是从对小众尊重延伸出来的一种抗拒吗?
这句话的前一句是「如果他们所说的就是对,那么可不可以不要」。比如我一开始从左手变成右手,是为了跟大家都一样,那么大家说的就是对的吗?如果大家说的就是对,我们在电视上看到很多人对女人丶小孩丶老人的不尊重,我可不可以不要;要画着大浓妆就叫做明星,那我可不可以不要。我经过了这么多传统教育丶世俗教育丶社会大众舆论的教育,长成现在的我,当然知道了很多游戏规则,但慢慢有了觉知,有了改变,也有了一些增加。
这条路不太好走,可我总是在选择不是很好走的路,我想这大概就是我生命的意义吧,也就不会去拒绝它了。好像说这次我要做荒岛音乐会,要将《房间唱游》延伸到内地去,此时此刻对我来说是紧张的。每个地方都有它们独特的文化丶人文和思想,我不晓得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大家对房间里的内容有什么感觉。如果就一般来讲,就简简单单地唱个歌就好了,何必还要传达这么多的东西?可偏偏我不是这样的人,我必须要花更多的心思去跟你们联结。我还不知道你们的长相,你们是什么样的心丶什么样的眼睛,我只能从自己出发,诚恳地去表达。让大家在熟悉的制式环境里,有一点不同的思考方向,我当然愿意。
本文原载:《城市画报》第236期2009年7月28日版
录音整理:刘嘉璇(实习生);图:大大树提供

29 Aug 2009
万芳·房间唱游──左撇子的提问歌本
同性爱丶地球变暖丶女性体验,万芳用发问的方式表态,关注「少众的丶异己的丶被忽略的丶不被尊重的」个体,把声音送给那些在人群里沉默不语的「异类」。这些提问,拼凑出一个阶段里完整的万芳。至于答案,她已在这些年的每日生活中一一给出。从下面的对话中,你或许能找到蛛丝马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