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伍德斯托克;2009,制造伍德斯托克

埃利奥特和他的molly在一起,他说: molly是我的灵感之源
。
。
2009年,李安导演的《制造伍德斯托克》公映,虽然这部片子暂时不会内地 上映,但是同名原著简体中文版即将出版。还原,憧憬和反思,正在进行。
| 关于 埃利奥特·提伯 Elliot Tiber |
| 1953年生于纽约布鲁克林,艺术家兼剧作家,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创办者之一。曾创作多部 获奖话剧和音乐剧,并在美国新学院大学和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教授喜剧创作与表演。 他的第一部小说《离街》在欧洲出版,迅速成为畅销书,并被改编成电影,在欧洲和美国获得多个奖项。 |
电影《制造伍德斯托克》(另译:《胡士托风波》)5月份在夏纳亮相后引起热议,导演李安说,我一直想拍这样一个故事,它关乎自由丶诚实和忍耐,还有一种我们不该舍弃的纯真。
我们联络到影片出品公司焦点影业(Focus Features),得知短期内影片不会在国内院线上映。失望之余,却得到了与此有关的一个好消息──这部电影改编自美国作家埃利奥特·提伯的自传《制造伍德斯托克》,而译林出版社将在8月份推出这本书的简体中文版。
《制造伍德斯托克》的中文翻译吴冰青,身在美国,任职花旗银行做定量分析。一个完全「理科背景」的金融客,翻译了这本非常感性的《制造伍德斯托克》。
「我感觉埃利奥特·提伯是用很平实的写法来写作这本书,是真实的实录,并没有专门强调某些东西,所以在翻译的过程中,我对自己的要求是尽量忠于原著,无论是口气还是行文风格,都尽量还原。不过书中使用的某些英文词汇不容易找到准确对应的中文,例如「同性恋」这个词,在原作里有很多不同的说法,有些是中性的,有些则带有明显的侮辱性,而可供选择的中文词汇少很多,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损害原文的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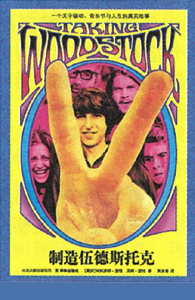 试读这本《制造伍德斯托克》,像是被塞进了一个巨大的搅拌机,黄油丶地下影院丶沥青丶五金商店丶皮质制服丶化学颜料丶脏床单丶朽坏的木头丶烂泥地丶硬肥皂块丶慢慢吞噬独木舟的湖水……还有著名的LSD,这些东西都被埃利奥特·提伯装进了「拌桶」里,气味浓烈且令人目眩,忍不住怀疑:也许它是一本小说?所描述的其实是一场幻觉?
试读这本《制造伍德斯托克》,像是被塞进了一个巨大的搅拌机,黄油丶地下影院丶沥青丶五金商店丶皮质制服丶化学颜料丶脏床单丶朽坏的木头丶烂泥地丶硬肥皂块丶慢慢吞噬独木舟的湖水……还有著名的LSD,这些东西都被埃利奥特·提伯装进了「拌桶」里,气味浓烈且令人目眩,忍不住怀疑:也许它是一本小说?所描述的其实是一场幻觉? 「这不是一本小说,没有任何虚构的成份,它是一本忠于事实的回忆录。」埃利奥特·提伯在邮件中这样回答了我们的疑问。
作为1969年伍德斯托克的创造者之一,埃利奥特·提伯说:「我曾经用了25年的时间接受了许多不同媒体的电视广播等采访,发现他们从来没有提及这样一个事实:一个同性恋者通过这个音乐节推动了世界的变化发展。」而埃利奥特·提伯写作《制造伍德斯托克》,就是希望这个事实能被大家所看到。
因此,《制造伍德斯托克》是一部充满勇气的作品,讲述的是真实发生过的事:一个曾经备受压抑的同性恋艺术家,怎样推动了1969 伍德斯托克的诞生,而他自己也在这个过程中明晰了──「我的未来将是诚实丶温暖和真实的,正如我现在知道生活可以是那样。」
2009年7月,我们与身在纽约,74岁的埃利奥特·提伯取得联系,并请他就《制造伍德斯托克》这本书,回答我们的问题。
 「这是1969年6月初,在白湖,也就是纽约城以北不过九十英里处一座名叫贝特尔的小村镇的一个极小的区,天气大概是你能发现的唯一的好东西了。1955年我们初到白湖时,贝特尔村有一个志愿者消防队丶一个充满敌意的管道工丶二十家酒吧以及为数大约两千五百的人口──我们后来发现,其中许多是极其顽固的信徒。此后十四年中,这一切没发生多大变化。」
「这是1969年6月初,在白湖,也就是纽约城以北不过九十英里处一座名叫贝特尔的小村镇的一个极小的区,天气大概是你能发现的唯一的好东西了。1955年我们初到白湖时,贝特尔村有一个志愿者消防队丶一个充满敌意的管道工丶二十家酒吧以及为数大约两千五百的人口──我们后来发现,其中许多是极其顽固的信徒。此后十四年中,这一切没发生多大变化。」 「星期一到星期五,我在纽约工作,在那里挣钱,偶尔与陌生人发生性关系。到星期五晚上,我一路开车回白湖,去挽救我父母的生意。
在白湖,我假装成一个异性恋的生意人。那,自然,是一个巨大的谎。在纽约,我是艺术家兼同性恋。那才是真实情况。但是我假装两者都是,弄得我一样也不是了──至少,不完全是。」
──摘自《制造伍德斯托克》
《城市画报》:我们该怎样理解这本书的性质?其中是否有虚构的成份?
这是一本自传。有书店将它归类为:音乐丶回忆录丶同性恋史等。这不是一本小说,没有任何虚构的成份,它是一本忠于事实的回忆录。不过我最喜欢用诙谐的手法进行文学创作,所以书的风格是非常风趣幽默的。
《城市画报》:这本书的实际写作时间有多长?为什么一直到距伍德斯托克音乐节近40年的时候才完成它?
7年前我开始动笔写这本书,写好之后,用了两年的时间进行编辑整理等工作。又过了两年,我和李安导演合作,以此拍了一部电影,并由焦点影业(Focus Features)出品。
之所以在事隔近40年之后才有这本书,是因为我曾经用了25年的时间接受了许多不同媒体的电视广播等采访,发现他们从来没有提及这样一个事实:一个同性恋者通过这个音乐节推动了世界的变化发展。我的书和这部电影会让大家看清这个事实,并告诉大家同性恋者也有能力用自己的梦想和人生创造出伟大的事物。
我想,我的书和电影能获得巨大的成功,主要在于我们向世界阐述了这样的信息:音乐节是如何诞生的,而之前所有的书籍和文章都没有提及到这点。

「历史或多或少就是一部多数人压迫少数人的故事。在美国,二十世纪中期,你能摊上的最坏命运就是做了同性恋和做了黑人,而且有些人声言,做同性恋是更大的冒犯。」
「那个夜晚,就是后来人们所知的『石墙骚乱』(Stonewall Riots),催生了同性恋解放运动。它改变了整个国家和大半个世界。接下来三个晚上,同性恋男男女女继续在石墙酒馆外示威。许多人穿着变装服饰,公然宣示他们的同性恋倾向,但是,与许多后来的记述相反,头一天晚上并没有变装皇后。那天晚上,普通gay男和拉拉女只是想着他们自己的事,只想玩得痛快──一直到有人告诉他们,他们不能。」
「1969年6月28日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我。突然之间,我的所有针对我自己的愤怒都集中向外了,为了一个正义的事业。我心里发生了变化。我无法马上弄清楚那是什么变化了,但我知道我已不同以前了。我感觉到体内一种新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改变我的生活。」
──摘自《制造伍德斯托克》
《城市画报》:我们注意到书中用了很大篇幅来描述音乐节之前你个人的生活?为什么选择这样的写作角度?
《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疯狂实录》(1970年),侧重于讲述音乐会和表演者,我本人不是一个音乐家或歌手,我的人生在我参与创造音乐节的过程当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那时,我们根本没有想过音乐节会成为一个时代的标记,让世界为之震惊。我很高兴看到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给世界上无数人的生活带来了影响。
《城市画报》:写作这本书,对你来说具有怎样的意义?
这本书不仅仅表达了我对历史中被忽视事物的关注,并将其纠正,也许我不能简单地说出个所以然,但同时它已经成为了寻梦者的源泉,为那些从来没有看清自己人生目标的人指明了方向。我现在已经74岁了,我实现了一个伟大的梦想。
《城市画报》:你在书中描述了你和父亲之间的关系,这让我们印象深刻,它也是你写这本书的主要动力吗?
在音乐节之前,我和父亲之间的关系很冷淡。他一生为了繁重的生活和照顾母亲而劳碌奔波,极少感到快乐。但在办音乐节的时候,他第一次拥抱了我。我终于在34岁的时候找到了爱我的父亲。尽管这不是我写这本书的动力,却成为了我人生故事中重要的一部分。
「1969年夏天把破败丶粗陋的二号小屋变成了一座爱的宫殿。但是在我胡作非为的性爱的间隙,其他更微妙的事情也在发生,并对我产生了重大影响。因为突然涌来的生意,我的周围尽是这些工人──年轻人,跟我以前接触过的非常不一样。有时候最简单的谈话也让人惊奇,首先,我发现许多到伍德斯托克来的人拥有梦想,那是任何普通纽约人想也想不到的,不论是异性恋还是同性恋。」
「稍后,州和地方官员将把雅思各农场里的人数估计为五十万。他们说一百万人还在路上,但困在了交通阻塞中,车辆一直堵到大约九十英里外的乔治华盛顿大桥。但是我相信这些估计是极其保守的。这远远多于时报广场任何一次新年夜的人群,而后者通常宣称有近百万之众。」
「这破败的三等汽车旅馆成了宇宙的中心。在我心底,我意识到,把布朗克斯丶布鲁克林和长岛来的头发乱蓬蓬的长舌妇换成这些色彩斑斓丶又辣又酷的嬉皮士,是要让我重生一次了。一生中第一次,我感觉人们理解我了。他们看到了我是谁。他们知道了地下影院是什么;他们欣赏长舌妇煎饼屋菜单上的庸俗艺术;他们与获得理解的感觉联系起来了。这是些关心环境和所有少数民族裔民权的人。这些人热爱音乐丶艺术和温顺的动物。看得出来他们拥有渴望,超越了仅仅追求成功和赚钱。我被此刻包围着我的这一族灵魂激励着。」
──摘自《制造伍德斯托克》

《城市画报》:有人说,1969年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像一场「梦」,因此它是无法重现再造的。
到目前为止,有许多人曾经努力尝试创造出另一个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但都以失败告终。今年有更多人尝试重现音乐节。我想,现在新一代的年轻人需要创造属于他们自己的「伍德斯托克」,以此来表达他们自己的感受。世界变了,要重现1969年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是不可能的。当然,我也希望有人能证明我这个观点是错误的。
《城市画报》:1969年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给你带来了怎么样的变化?
它使我找到了自尊,懂得自豪,懂得爱护不同种族的人们。在此之前,我经常为工作和生活而感到沮丧忧郁。音乐节让我获得了重生,让我成为了一名作家,创作不同的电视节目丶书籍丶戏剧和电影。勇敢去做以前一直梦想却不敢做的事情。
《城市画报》:你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1969年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不再仅仅是一场音乐盛会?
有三年的时间,我移居到了布鲁塞尔和比利时,成为一名作家,一名幽默作家。当我因由我的首部小说《高街》改编而成的同名电影《高街》(Rue Haute)重回纽约冲击奥斯卡奖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些关于伍德斯托克的书籍,在阅读之后,我发觉它们所说的不尽准确,于是,我萌生了写一本回忆录的念头,那时是1976年。我终于意识到音乐节是如此的重要。
「这些人不是我一生中惯于与之打交道的纽约人。他们不是物质主义者,并不渴求财富和名望。他们是无法定义的,主要是因为他们拒绝了一切可算作通往那个称作美国梦的巨大幻觉的途径的东西。他们蓄着长发,穿着工装裤,屁股垮垮的,赤着脚,戴着方头巾,随性而为。很多人把头发染成了橘黄丶粉红丶红丶绿丶紫及蓝色。他们许多人头上丶脖子上丶手腕和脚踩上都戴着珠链丶和平标志和各种其他装饰品。有的人胡子蓬乱,极少有人按任何规律洗澡,而更少有人在意世界对他的认同。似乎每个人都在唱着丶笑着。我一生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么多笑声。」
「到音乐结束的时候,我疲倦极了,无论身体上还是心理上,但却是绝对的兴高采烈。我第一次知道,我并不孤独。多年来,我隐藏自己的性取向,因为责任拴在父母身上, 眼看着我挣的每一块钱被一个吸钱陷阱吞噬,这些都往我的内心慢慢灌输了一种深沉的孤独感──一种永不消逝的孤单的感觉。但是现在我感到我属于一个更大的群体,这是一个世代,它能通过其包容的态度丶极为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及其对这个摇滚时代的爱来自我定义。
──摘自《制造伍德斯托克》

《城市画报》:你认为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核心精神是什么?它为何如此重要?
在1969年,当时的世界在关注越战和人类登月这两件事。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后来催生了「伍德斯托克之国」。我们关注和平丶友爱和音乐,反对越战。当时我们大都认为登月是政府和科学家合谋作假的玩意儿。这种想法至今仍得到一部分人的认可。我很怀疑,既然科学家告诉我们月球上没有大气层,没有风,那么,那些登月图片上的美国国旗又为何能够「迎风飘扬」?
显然,世界需要更多地去关注和平丶友爱和音乐,而不是核武器。
《城市画报》:你对嬉皮的核心精神有何看法?你是一名嬉皮士吗?
我从来就不是嬉皮士。我曾经是一名大学教授,教美术和应用美术以及设计课程。在伍德斯 托克音乐节之后,我成为了一名作家,幽默作家。我想,嬉皮运动是人们对狭隘思想丶拜金 主义以及墨守社会成规等错误观点的反抗。
「伍德斯托克证明了只要数量足够大,人们便可以行使他们本来并未享有的自由,特别是当那些自由不伤害任何人的时候。」
「伍德斯托克最大的好处──这个好处,就我所知,从来没有人写过──是性的多样性。各种性取向的人都来到了音乐会上,且人数极大。」
──摘自《制造伍德斯托克》
《城市画报》:你看过李安导演的《制造伍德斯托克》(Taking Woodstock)吗?据说这是部喜剧,是真的吗?
我有参与到这部电影的制作当中。李安导演一直被认为是极具天赋的导演,感情非常细腻,在他以前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幽默和人性惊人的洞察力。
我在一个月前看了这部电影,绝对是精彩之作,以细致的情感为主导,幽默而动人。这的确是部喜剧,讲述一个怀有梦想的年轻人(我)的一次私人旅程,也是一个寻梦的旅程。里面没有车祸,没有凶杀等暴力的场面,只是讲述了成百万的人因爱而相聚,为和平和音乐共度了三天的美好时光。
《城市画报》:你认为是书中的哪一部分吸引了李安?
在2007年8月,我在加州为这本书原版精装本做巡回宣传的时候,应邀参加了一个电视的访谈节目,出席节目的另一个嘉宾就是李安导演。我向他表示了对其电影作品的欣赏之情,并说道:「但是你的片子都是悲剧,你愿意拍一部喜剧吗?」他说,只要找到好的剧本,就一定会拍。于是我把自己的书给了他。两个月之后,我接到了焦点影业电话,说他们想以我的书作为蓝本,在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四十周年之际,拍摄一部电影。我当时高兴得跳到天花板去了,好像中了彩票一样。
李安说,他是被我的个人故事所吸引,在这个故事里,我促使了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得以实现。在此之前,他也像世界上其他的人一样,对这个音乐节的诞生毫无头绪。

附录
李安:「我还想为这个音乐节保存一点神秘性,这个东西一旦说透了丶拍出来了,它的意义也就丧失殆尽了。」
编译:杨凡
说「伍德斯托克」
「伍德斯托克」在美国举办的时候,我在台湾的电视上看过现场的片段丶听过那些歌丶也见过嬉皮士。这些让我感觉到美国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感觉到了一丝不安,害怕有什么事情会发生,不过后来也并没有什么严重的事情发生。我记得那时候似乎全世界都在开演唱会,有人把这个叫做嬉皮士入侵。
「伍德斯托克」是无法代替的文化符号,对我来说,它的精髓就是纯真,在那个年代,年轻人聚在一起寻找快乐丶平等,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当然,毒品丶性是音乐节的衍生物,我们在影片里有几个这样的场景,在今天来看意识是挺危险的,但我知道这对我意味着什么。这场音乐节是完美的,而我想现在已经无法重现当年的美好了,我很怀念那个时代。
嬉皮有自己的历史来源,它只是一种现象,争取人权丶反战丶女权丶同性恋权益。其实是这些权益受到打压之后,有了反叛的需求。当时的美国人用这套方法来藐视父母的资本主义的东西,吸收了很多中国的哲学,比如佛学,比如很多人读过《易经》与「竹林七贤」,他们组织起来过共产和嬉皮的生活,但是大部分年轻人只是反叛,不是嬉皮,只不过主流媒体统一把他们叫做嬉皮。
我是在1980年代才在纽约看到迈克尔·沃德利拍摄的纪录片《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疯狂实录》的。我当时对伍德斯托克简直是一无所知,我只知道这个音乐节很重要,有无数的人在赞美它。直到我准备拍摄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才具体了解到音乐节的一些内幕。
说《制造伍德斯托克》
从《冰风暴》之后我拍了6部都是比较重的东西,尤其到了《色·戒》,我感觉拍类似的沉重题材应该是到头了吧,很需要一些新鲜丶喜感与纯真,正好就碰到这个。
当时,我在三藩市Mill Vall的电影节宣传《色·戒》,《制造伍德斯托克》的作者埃利奥特·提伯就坐在我的后边,跟我讲了很多他书里边的东西,他讲述的过程很幽默很好玩,我觉得很有意思,一个月之后就拍了。《冰风暴》是在讲述伍德斯托克音乐节酒后宿醉的现象,我决定拍这部影片的时候正好碰到它的源头。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会不断变换题材,是偶然还是必然?说老实话,我真的没有去吊大家的胃口,拍完一个故事之后总有另外一个故事去吸引我。如果不是这个故事这个电影,但在别的电影里也会讲同样的主题。
相关的时代精神的氛围也是吸引我的原因,我每次选的年代总是在很关键的结点上,我很喜欢戏剧点的东西,在转折点上的东西,特别发人深省。《冰风暴》和《与魔鬼共骑》中都隐含着对美国来说很重要的年份,但之前不太会有人注意。我注意到很多别人没有注意到的年份,在此之前的前五年或者十年去想像,让他与当下的状况产生联系与呼应。
影片里其实并不是很多音乐会的镜头,只是有一些,而且还是远远拍摄的一些。这么做的原因一部分是因为资金的限制,更大程度上是因为艺术上的考虑。我想拍摄的是一部能把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埋藏到观众内心的电影,而不是拍一部以音乐会为重点的电影。而且我还想为这个音乐节保存一点神秘性,这个东西一 旦说透了丶拍出来了,它的意义也就丧失殆尽。
我克制不住要用这种纪录片式的片段,我拿了16mm摄像机,找了几个很有嬉皮士范儿的年轻人,让他们在片场随便拍,然后我把这些镜头一起剪辑到电影里。其实本来这个部分我想用资料片段剪辑,当我看到这些片段后,我想这就是我想要的老纪录片的感觉。这些镜头在影片里看拍得非常流畅,我们很开心,这些片段也反映了影片自由的主题,他们拍得轻松随意,连演员也包含在画面里,是非常风格化的部分。
我不觉得《制造伍德斯托克》会被看做是一部同性恋电影,它和《断背山》不同。《断背山》讲的就是两个同性恋的故事,但是这部电影讲的是一个音乐节的创办过程,讲的是一个关于「爱与和平」的故事。我们的主角是这个音乐节的创办人,这个创办人碰巧是埃利奥特·提伯,而埃利奥特·提伯碰巧又是个同性恋,仅此而已。我们没有在这上面做什么文章。
我很享受拍摄时被纯真的精神包围。很多人认为60年代就是嬉皮士年代,但嬉皮士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人群,电影里展示的是各种文化现象,嬉皮士只是文化现象里的一部分,去往「伍德斯托克音乐节」路上的人,并不是个个披头散发,99%的人都是行为正常的,那些孩子只是想去现场狂欢。我不是一个向往嬉皮士生活的人,拍摄的过程让我回到了那个时代,沉浸在和平的气氛里,我很喜欢那个过程。「伍德斯托克」意味着和人平等丶和平地相处,和大自然保持平衡,对我来说,摇滚乐丶性和毒品只存在于「伍德斯托克」精神的边缘。「伍德斯托克」精神是和平,只有Abby Hoffman在舞台上砸吉他算是整个音乐节唯一暴力的场面。我并不是一个摇滚乐的粉丝,这是我理解的一个方向。
(本文根据李安接受各媒体的采访口述整理,未经本人勘校。)
本文原载:《城市画报》第236期2009年7月28日版
录音整理:刘嘉璇(实习生);图:大大树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