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有人得到了什么,而学会沉默。
坏的血液掏蚀免疫系统,初期急性感染,在身体四处绽放斑斑红花。
拿个不能言的秘密往树洞去说,说完了,世界继续旋转。定时服药,控制如自由落体的检验数字不再往下掉。回神过来,意识到所爱之人端坐餐桌对面,秘密讲完了,他起身离开。什么时候开始,感到自己不洁。学会沉默,但沉默并不带来痊愈。日子一天天坏,偶有疏忽的药笺纸袋泄漏了事实,手指眼神抛过来,彷佛这世界洁净得过份了,不容污秽留存。
人们说这些有病之人不值得宽宥,他们有罪。听久了,分不清楚坏的是日子是世界,还是自己。坏得不该存在。
我的朋友是否也作如是想?
几年前,他验出阳性反应。但我不属于最早知道的那群人。
那一阵子,我们还青春。十八丶十九丶二十岁,正是新芽抽长,要伸出触角探索城市的速度与金属的时候。正为整个世界边边角角上长着的光彩蕈类感到兴味。身体是丹炉,倒进尼古丁丶酒精丶咖啡因,倒进知识丶忿怒与哀愁,倒进一切好与坏的。
原先走在类似道路上,后来却望向不同风景。我把还没看的书放在桌子右边,把看完的放在左边,他总笑我,就光会坐在咖啡馆的吧台看书写字,说为什么不多饮一杯酒。说我还没有过一个男人,算不上认识自己的身体。谈笑晏晏他说,他敲打身体变换各种姿势,透过迷幻的练习与工作,证明自己存在。他说,你有没有过纯粹的快乐?便邀请我在偶尔的深夜进入舞厅,黎明时离开。一起用完早餐,他拨了电话,继续走进日正当中的城市,遁入另一个黑暗的房间。回程捷运上,我想像他脱去衣物底裤,留下精液与汗水。那一阵子,在他身上我刚认识这世界无光的一面,领着我同陌生男子们在陆上行舟,在地底交欢,天亮后头也不回离开。
此间一刻,谁都希望快乐能永恒,以为世界不会消失。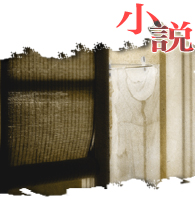 却总是不乏猥琐的耳语,说我们所站之处是豢养着病菌的索多玛城,说,地底相爱之人是要受天谴的,我听着那些,回说这有什么。但大过年的,新闻里报出警察突入私宅派对,清一色男体肉身排开,记者哇啦啦说着巷弄内的民宅变成毒虫天堂这里保险套散落一地空气中弥漫着精液汗水混合的体骚警察进入摇头派对时候狂欢的男同志抬起迷茫眼神彷佛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哇啦啦,我眼见那些半裸男子蹲踞低头,各色内裤在萤幕上阵列,好像七彩斑斓的花蕊毒蕈。过了几天,又见电视新闻上,卫生单位主管露出骄傲表情,说查获派对三成人口是带原者可谓对于爱滋防治大有斩获……我感到恐怖,揿了遥控器转台。什么事情隐隐然在我心头扎着。
却总是不乏猥琐的耳语,说我们所站之处是豢养着病菌的索多玛城,说,地底相爱之人是要受天谴的,我听着那些,回说这有什么。但大过年的,新闻里报出警察突入私宅派对,清一色男体肉身排开,记者哇啦啦说着巷弄内的民宅变成毒虫天堂这里保险套散落一地空气中弥漫着精液汗水混合的体骚警察进入摇头派对时候狂欢的男同志抬起迷茫眼神彷佛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哇啦啦,我眼见那些半裸男子蹲踞低头,各色内裤在萤幕上阵列,好像七彩斑斓的花蕊毒蕈。过了几天,又见电视新闻上,卫生单位主管露出骄傲表情,说查获派对三成人口是带原者可谓对于爱滋防治大有斩获……我感到恐怖,揿了遥控器转台。什么事情隐隐然在我心头扎着。
疾病的阴影挥之不去。那之后,我开始少往人声欢悦杂沓的地方走动,要肉身战场的金鼓之声离我远去。学会收束生活,假装自己不曾在生人面前宽衣。我不再同神明掷筊,说服自己,抽到大凶的不会是我,不要是我就好。
可是大凶签确实存在。某天,一个同我算不上十分熟稔的家伙,在网路上传来讯息便唐唐突突问,你是不是认识那个某某?我漫不经心说是啊。讯息回传来问,熟吗?我说,还满要好的,怎么了?对方字句中间不用标点符号一口气打完,欸那你有听说他嗑药滥交搞得年纪轻轻就中奖了吗你千万要小心少跟这种人来往……我没回过神来,问,什么?随即明白了,他是要说个不能言的秘密,不能言的HIV。我胸口像给什么掐了一下,听不真切。
啊,他是这种人。一瞬间,我几乎矢口否认那个某某,正是我的朋友。
我的朋友,不知何时成为了带原者,而我甚至是从别人口中听闻这件事的。偶然间发现那笺注记了命运的签诗,在我朋友的口袋里给胡乱地塞折,而我只能不安地看着,什么都无法改变。
我开始在朋友的话语中找寻蛛丝马迹。想他现下快乐是真实的吗,或者不是。他必然正对我隐瞒着什么。每次吃饭谈天,端坐对面,他为什么不告诉我?
一天晚上,我们再度吞服药锭,要陆上行舟。电视机萤光茕茕播送消息,记者俐落口吻叙述,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国道三号二百三十六公里处知名女艺人疑因未系安全带而在车祸发生时冲撞头部送医时已无生命迹象……我的朋友讲话像嚼口香糖说,好可惜,那么漂亮欸。我觉得晕眩,喉头哽着一句话不知道该说不说出口。我的朋友操遥控器反覆在新闻台间跳跃,顺手抄起不锈钢盘上的信用卡,在白粉堆间研磨,织成白索条条,问我要不要?我霎时以为那是丢给溺水者的绳,低声回说,不。不。他突又去接了记者话头说,干,那么漂亮一个人就这样死了。然后关闭电视,整个房间再度剩下飘忽的烛火。
我闭上眼睛,深深吸一口气。欸我问你哦。
怎样?
你最近身体状况是不是不太好?
还好啊,怎么了,问这个。别人跟我说,你出去玩的时候,中了。干,这些人就爱八卦。但是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想我能说吗?听听你那是种什么语气,能告诉你吗?
对不起丶对不起……我情愿把舌头咬断了吞下,换回刚讲出的话。
我的朋友眉头低低,说玩了这么多年,败在一个自己爱的人手里。一个让我的朋友认真想定下来的男人,一个,不烟不酒不药的男人。那时他俩认识,以为只是身体交欢很快要往反方向离去,但并肩走往台北城各处,或共享明亮室内一个典型的早晨,一壶咖啡,烘蛋火腿,焦脆的烤吐司种种,反覆想着其中经过的什么,就知道真是爱了。几个月后,两人租下一户小公寓,搬进去那天,男人同我的朋友说,我们今天不戴,好不好?
我的朋友说,爱到了就爱到了,拿掉保险套那一瞬间像玩朴克牌抓鬼。抽牌的时候要记得微笑。里面的鬼牌不宜过多,但也不会太少。抽完离手,翻开来,愿赌服输。
但我的朋友又露出一贯的笑容说,他的世界没有崩解,时间没有停止,他的日常继续前进,不特别快,也不特别慢。说来其实不难。他每隔几个礼拜得上医院拿药,抽血,说每次验的都是同一件事,扎的也是同个地方。只是扎久了,手肘内侧大血管处,便常时透着不会消褪的血瘀。CD4淋巴球指数打印在检验报告的同样位置,报告书拿了就看,指数上升了便为自个儿欣喜丶指数下降了要仔细反省,是否轻忽了服药的时间,都好。都好。
他独力承担药物的副作用。腹泻了,掉发了,像洪水毫无预警地泛滥,天晴以后,一肩扛起自己爱情的遗迹。
我的朋友并不避讳谈论死亡。他说,疾病并不让他变得虚弱。
让人难过的是,人们要他什么都别再多说。心头一惊,我的朋友究竟同什么东西在对抗着?
年节时候,人们问他交女友了吗?为什么不用当兵?当他诚实说起自己CD4指数已失控地下降,人们掩耳走避。人们禁止我的朋友谈论身体,却指着他背影说,天谴者。禁止他谈论爱,好像他的爱是污秽的。人们不愿听他谈论死亡,但丢出的言语灼灼,又何尝真正伸出手去帮助他远离死亡?避而不谈从不代表痊愈,好比白晃晃的医院里楼层并没有四,还是持续有身体被推进太平间。带黑色斑块的身体。肺部被病毒浸润的身体。在车祸中缺手断脚的身体。被癌细胞啃食殆尽的身体。生死边界晦混不明,身体既已成为断简残篇,为了什么理由,生者还要再去区分死亡的高贵或低贱?
如果真的有,我情愿,那会是个真正重要的理由。我的朋友说。
感染者失去了他们的名字。人们的眼神扎过来,却是读着他们新的名牌,啊这人是带原者,是爱滋宝宝,是男同志是毒虫,是被针扎的医护人员,是守着自己丈夫却被他不戴套野食给传染的家庭主妇,是输血感染的病药受害者……谁还在乎他们当初如何感染。都不重要了。人们读着,沿曲折走廊走入感染科的背影,读着卫生所人员在信箱门口张贴的寻人启事,人们从中读出什么,若有所思摇摇头,嗳,这种人。谁还在乎当年,朋友的男人也是因为单纯地相信,而放弃了该有的防备。
感染,一则坏的隐喻。是怎样的眼睛看着他们,带原者背着自己新的名字,走进人群的隐没带,要拉拉衣角遮掩。缩小些,占用捷运月台更少的空间。坏得彷佛自己不该存在。
我想起电视新闻里,卫生局官员的表情。
那是一张欣慰的脸。彷佛在说,抓到这种人,我们的世界就安全了。我们的世界再不会被这种人给污染了。好像,有个声音从他上扬的嘴角止不住地泄出来,这些毒虫毒虫毒虫毒虫毒虫毒虫感染的血中带有病毒的肮脏的毒虫毒虫毒虫毒虫毒虫都要揪出来他们最好不要存在……这种人。活该。自找的。不检点。人群丢掷的词汇如巨石般从天空落下。
我突然懂了,人们伸出戟指的手,从来不需再有什么其他的话。而他为什么选择不说?答案清楚明白。当我揿下按键转台不愿再看新闻,当我意图否认他是我的朋友,便成为人群的共谋。
我其实也在妖魔化我的朋友。
他得到,他沉默。每天每天,戴着面具出门。
我的朋友说,感染后自觉在城里活得像句脏话。他不能爱。他说,他穿上件黑色衬衫像穿着丧服,到人群里头,给自己服丧。
病毒不问季节,鬼火般烁迷迷给人指路,终要满城夜行的不眠者失了方向。我的朋友本来性格坚定丶执拗丶顽强,但时间,时间将他一丁一点儿地变小,像是要回到孩提时代那样,要将他缩小到足以放进一口儿童棺材里去。如果倒回成为儿童的他,能摆脱一切恶的言语,我想,也算是值得。
他一天天走向死荫的幽谷,但我们之中,又有谁不是呢。健康丶病朽,我们终究不能抵挡这身体终要老去,也总有一天会躺在棺柜里,等着别人来看我们一眼。却还有什么事情是重要的,庆幸我的朋友同我分享了秘密,要我听完,同他对分了,担着,证明他不孤独。
那年同志游行,众人风华妖冶地为「生」的权益踩街去了,我的朋友站在人声鼎沸的街头,举着牌子写「FREE HUGS」,索求简单的拥抱。如今想来,他身体虽弱虽瘦,领着标语牌告前行的背影,带着宽慰庄严。如是我知道,要他死的从来就不是病,而是人群。人群是患者们一生的功课。当尘归于尘土归于土,即使人群不曾谅解我的朋友之生丶之死,我知道的,他街头兀立的姿势之所以决绝,为的是告诉人们生之困窘,生之灾厄。要人们看透,病症不过一则恶的隐喻。
拥抱,为的是要人们看他双臂张扬。
危颤颤地臂弯打开,竟也有花。
后记:
这篇文章一部份是纪实,一部份虚构。纪实与自省写给我的朋友,虚构的光景则写给我不认识的那些人们。当我问我的朋友,有什么事情是我可以帮你的?他笑着说我成天只会写那些都是字的东西,能帮得上什么忙?于是我有了这篇文章。
祝福您幸福健康。
本文原载:罗毓嘉部落格「婴儿宇宙」
http://yclou.blogspot.com/2009/10/blog-post_25.html












 列印版本
列印版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