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機場出口處有一個當地的民間樂隊,黑紅臉龐的男性樂手正在用排簫演奏一首悠揚和高遠的民謠,搖著響鈴的女歌手,哼著我不懂的歌詞當和聲。聽著相當耳熟,一時間卻想不起這首歌的名字。
我秘魯之行的後半段,導游帶我們去了一個著名的大峽谷,觀景台是專門用來看飛鷹的。我才猛然想到,我在機場聽到的秘魯音樂,正是經過美國歷史上最著名的男聲二重唱組合Simon & Garfunkel改編過的秘魯民歌《山鷹飛去》(El Condor Pasa)。
此刻,我在電腦鍵盤上,書寫自己的這段記憶,找出這段美妙的純粹的音樂,用Media Player播放著,安第斯高原的氣息,撲面而來。這樣的民謠,流傳到全世界,讓一個中國人後裔也耳熟能詳,居然要有賴於強大的美國流行文化,做包裝,做推廣。很有意思的一種現像,是吧?
出了機場大門,迎面是一塊碩大的廣告看板,是一個南韓電子公司的形象廣告,並不推銷任何一種具體的產品,廣告人就可以發揮得比較天馬行空一些。主題是家用電視機的「進化和演繹」,一系列的廣告形象,抱著從大肚皮的笨重陰極管電視,到輕薄的LCD平板電視機。這些代表各個時代的廣告形象,是借用和隱喻從猿到人「進化和演繹」的猴子,猿,類人猿,人。
跟世界上其它所有異性戀男性霸權中心的地方沒有兩樣,Man就是人,男人就是人。畫面上,「人」的進化,也就是「男人」的進化。這個廣告上,我的眼睛從左到右,從猿到人,略過匍匐在地四腳長毛的野獸,直接落在畫面最後那個直立行走的男人身上。

性的巨大能量啊。
只不過,我把這份性的能量對我眼睛的衝擊感受,保留給我自己。秘魯之行,跟我同行的是兩位我在互聯網上發帖子找到的遊伴,一對華裔加拿大兄妹。
人在旅途,時時刻刻都有強烈的眼睛衝擊。對我而言,美男的美,則永遠衝在最前方。
我聽著那首熟悉的樂曲,看著一個秘魯民間樂隊,卻因為廣告牌上美男的誘惑,我都沒注意到,吹排簫的秘魯民間樂隊,樂手們都穿著古印加民族的傳統服飾。
最有特色的是他們肩上的披毯,一排排簡單條紋的顏色,設色非常大膽而質樸。和世界上其它古老樸素民族一樣,使用的是非常純正的顏色,直接的大紅大綠。那些微妙複雜的復合中間色調,大概在他們的古樸文明中,還沒有這種嬌柔造作的複雜概念。色彩就是非常直觀的純色系,艷麗,艷俗,鮮艷,大俗大雅,童心未泯,有種天然童趣。
當時我沒注意到,但此刻,我坐在加拿大多倫多我自己的電腦前邊,這篇文章我預先構思好了,來寫我的秘魯遊記一個片斷的時候,記憶中的那種色彩,還是那麼生動活潑。這樣強烈色彩對比風格的服裝和家用裝飾,在秘魯隨處可見,無需費勁深挖我的記憶,樂隊歌手們的艷麗披毯,此刻還是在我的腦際,一串樸實的純色條紋,跳躍著,熠熠生輝。
還有一個原因,那是彩虹的顏色。
和我們同志高舉的彩虹旗幟,簡單鮮明,單純強烈,理念如出一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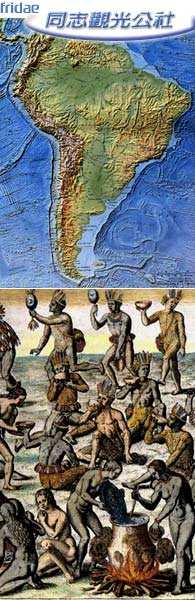
位於安第斯山高原的世界著名古都庫斯科(Cuzco),海拔3,350米,名列聯合國人類自然歷史遺產名冊,已經成為全人類的共同財富。
在預訂的旅館稍事休息,我的旅伴就迫不及待地邀我,一起游覽這個融合了古老印加(Inca)文化和西班牙殖民者文化的歷史文化名城。
我們事先有一個分工合作的約定:
哥哥擁有一台非常高級的膠片照相機,有點專業攝影的味道,用彩色反轉片,負責旅途風光風土人情的幻燈片攝影製作;
妹妹用的是小巧的數碼相機,外加一個大容量的移動硬盤,哢嚓哢嚓想哪兒照哪兒,每天都把數碼照片轉到硬盤上,這樣就不用擔心記憶芯片的記錄容量了。她負責「到此一遊」連人帶景的留念照片。
我帶的是Mini-DV攝像機,負責活動圖像的旅游記載。
多虧了我負責掃來掃去搖拉推移拍過不停的錄像,要不然,我一個男同志,赤裸裸地直盯著帥哥美男靚仔,不管不顧,見了誰英俊就鏡頭定在那兒,拍個不停,哈哈,我不介意兄妹兩知道我的同志身份,不過是人在旅途,真是說不清道不明的尷尬哦。
我的攝像機鏡頭,輕描淡寫,漫不經心,有意無意,不斷地「掃」過任何一個有趣的景致,而不是明目張膽地只固定在人類的雄性成員上。
走在庫斯科古城的大街小巷,那些廣場,民居,那些遺蹟,殿堂,我們看到那些讓人嘆為觀止的古老石頭建築,尤其是西班牙的入侵者,在印加宮殿廢墟的石頭地基上,建造的天主教堂。在昏暗香火繚繞的聖母雕像或畫像面前,我好像是走進一個悠遠古舊的夢中。
三人且行且議,心閑氣定,沒有一點疲態,嘻嘻哈哈地說,導游手冊上對高原反應的提醒和警告,實在有點大驚小怪小題大作,看看吧,我們仨,不是都好好的,氣促?心慌?沒有的事情嘛!
庫斯科同時也是個山城,稍微登高望遠,就可以居高臨下地看見房屋建築的屋頂,看見公共建築屋頂上的旗杆,看見旗杆上掛著的旗幟。
我四處掃拍的攝像機鏡頭中,出現了那兩面旗幟的時候,我感覺到我人生中的第一次心悸氣短,我訪問的第一個高原城市,傳說中的高原反應,真的就這麼不速之客地光臨在我身上了麼?
首先掃到的那面旗幟,紅白兩色,旁邊的兩道紅色豎條夾住中間的白色豎條,風不大,旗幟沒完全飄起來,隱約有什麼圖案在中間白色的底子上。
這是不是加拿大的楓葉旗呢?
庫斯科是我從多倫多出發秘魯之行的第一站,十多個小時前,我還在楓葉之國加拿大的國土上。這一刻,我的攝像機鏡頭中,居然就是紅白兩色三條紋的旗幟高掛,好像是時光倒流,昔日重來,如夢似幻地,剎那間,就夢回加拿大了。
攝像機的鏡頭是20倍變焦的,我定了定呼吸,顫抖著手,變焦拉近一看,風把那面旗幟飄開了,紅白旗幟中間白色條紋上的圖案,不是親切熟悉的楓葉。心悸稍微平息了一些,從重回楓葉之國的奇妙夢境,猛然醒來,猜測覺得應該是秘魯的國旗吧。
國旗所代表的國家,和族群,和家庭,和個人類似,一樣是有強權有霸權有弱勢有少數的。加拿大倒是很少在世界大舞台上持強凌弱稱王稱霸,不過呢,也仗著時不時地被聯合國派遣,外出派兵維持和平,把個紅白兩色的楓葉旗幟,插進了地球上的很多熱點角落。
拉丁美洲的秘魯呢?美國後院的秘魯呢,我知道出了一個日裔總統藤森的秘魯呢,我已經足踏這片有過璀璨文明的土地了,怎麼會對秘魯這個國家的這面國旗,居然會是一無所知的無知?

如果我的鏡頭有情感的話,那一刻一定是滿懷我對自己無知的愧 色,和對這個魅力無窮國度的虧疚之情,慢慢掃過紅白旗幟。我攝像機的取景框中,出現了另外一面旗幟。
在同一建築的屋頂上,就在紅白旗幟的旁邊,有另外一面旗幟,讓鏡頭後邊我的眼睛,一驚一乍地張得老大,心跳得比剛才以為夢回楓葉之國的驚悸還快。身邊是毫不知情的兄妹旅伴,多虧了有手持的攝像機擋在眼前做掩護啊,讓我不同尋常的失態,就這麼繼續毫不知情下去。
就在那個殿堂的屋頂上,堂堂的一國國旗旁邊,另外一根的旗杆上,飄著同樣大小的另外一面旗幟,我大驚小怪目瞪口呆地,在數碼攝像機的取景器中,看見了高高飄揚的彩虹旗幟!
耶,沒錯,是彩虹旗也!
在我自己的城市多倫多的同性戀聚集地,在那條同志街上,我已經對彩虹旗幟,司空見慣見怪不怪了。遊歷過號稱最先進的幾個北歐國家,和美國的幾大同志首都,即算是自由開放,平等民主,同性婚姻都完全合法的加拿大,我還真沒見到:第一,公共機關的建築上,高揚飄動彩虹旗幟的;第二,彩虹旗幟,可以並肩掛得跟國旗一般大的。
這個秘魯啊,這個庫斯科古都,真的就解放奔放豪放到如是地步?
驚訝驚奇驚艷,我都要暗下決心了,如何找個借口,今夜就擺 脫這兄妹倆,獨自拜訪這棟國旗和彩虹旗幟共一色的建築,難道,我千辛萬苦地讀萬卷書行萬裡路,總算是來到我們同志的天堂樂園?
但是,但是,但是……
還記得我前邊的伏筆麼,那個被我忽視略過的印加民族傳統服飾,那個我用了不少形容詞來比劃那種純色設置色彩的肩上披毯?彩虹的色彩?
是的,和世界上許 多古老或質樸的民族一樣,印加民族對天際上出現的神秘瑰麗的彩虹,神出鬼沒來無影去無蹤的彩虹,有種莫名的敬畏和崇拜,認為是他們一直崇拜的太陽神,送給人世間的禮物。甚至,有他們景仰的彩虹專屬的神袛。
我們中國古代的說法,說天上的虹,且是霓虹霓虹,虹為雄,霓為雌,是會吸水的龍,龍啊,夠敬畏吧!
這個古老的印加民族,遠在西方文明發明創造的「同志」這個概念之前,遠在西方同志賦予「彩虹旗幟」那麼多自豪的含義之前,遠在同志們把多姿多彩的彩虹旗幟披掛在身上,行走在大示威大游行的群眾運動之前,一直都在尊崇他們自己文明中的彩虹神聖形象,一直都在按照他們自己口耳相傳代代相傳的理解,來闡述他們心目中的彩虹含義,彩虹像征。
自己曾經是南美強權霸權的印加(Inca)帝國,占領和統治過南美大片土地,卻在更強權更霸權的西班牙葡萄牙入侵者的槍炮和聖經的雙重攻擊下,變成過眼雲煙。印加文明中的活化石活遺跡彩虹旗幟,也是遲至1978年,才由庫斯科市政當局,正式認可,宣布古老的彩虹旗幟是他們那片古老印加國土的像征,以此來宣示印加民族對自己文明的歸屬和擁有。
很有意思的是,如果說到印加官方的彩虹旗幟和同志彩虹旗幟,龜兔賽跑,誰先誰後,其實是同一年。乖乖呀,也是1978年呢,一個住在美國舊金山市的同志藝術家,也是一個同志活動家吧,Gilbert Barker,設計製作了世界上第一面作為同志自豪像征的彩虹旗幟。
兩面看上去大同小異的彩虹旗幟,其實還是有異的,同志自豪彩虹旗,是六色六個條紋,印加歸屬的彩虹旗,是七色的,比同志旗幟多了一個白色的條紋。












 列印版本
列印版本










讀者回應
搶先發表第一個回應吧!
請先登入再使用此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