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朝十时上班,走过长廊, 总有几个男人「细声讲丶大声笑」,那就是大班(郑经翰)丶黎则奋丶小明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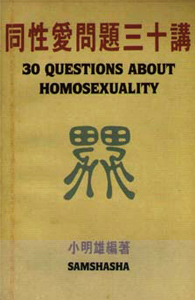
有一趟我想做一个爱滋病的专题,小明雄自动请缨,一手拿了几本有关爱滋病的书给我参考,那些书的作者,名字记不清楚,我花了十日才看完,他又把我拉到餐厅,然后滔滔不绝向我讲述香港有女童找不到HIV的个案……美国药厂的暗谋……同志并没有经营爱滋病的专利权,然后讲到非洲的猿猴也发现爱滋病等等。
那天在场的还有他的男朋友,到此我才明白他的同志身份以及为何如此关心我做的题目。他又教我到卫生科接受AIDS的测试,看看我将会有什么待遇,哎! 结果……结果是怕自己的经验可能不具备代表性,便召集帮手,后来几乎全编辑室都做了测试。
到最后我也是花了几个晚上,写了大约一万字关于爱滋病与另类治疗的题目,结果,跟小明雄当记者时遭遇的命运一样,被老总黄国华剪掉了四分之三,理由是太泠门,于是便转向港闻专注的课题「接受AIDS测试者该当何罪 社会卫生科令人却步」。香港媒体真的没有累积,过了五年,我仍看见在别的报纸做同样的题目。
改变对同志的印象
我曾碰过不少男同志,有过无缘无故被怒目而视的经验,有人告诉我因为他们憎恨女人抢走他们的男人。小明雄除了那件紧身T恤,我找不到任何疑似gay的踪迹,他不肯在我的专题中接受访问,不肯拍照,他肯定不是俊男,但和霭可亲,「肥淋淋」的身驱散发着阴柔的亲和力,如果闭上眼睛,我会向他倾倒,坦白说,认识他改变了很多我对同志的印象。
那一年,他对我说自己患了绝症,说时张开两手坦然得像诉说别人的事,当时我看着他们,对死亡的课题显得非常平静,平静得像个信徒。
本文原载《文化现场》2008年11月号第7期











 打印版本
打印版本










读者回应
抢先发表第一个回应吧!
请先登入再使用此功能。